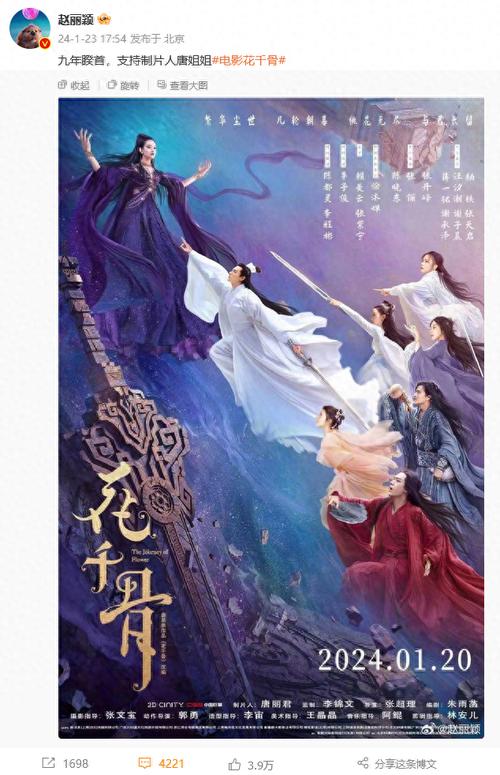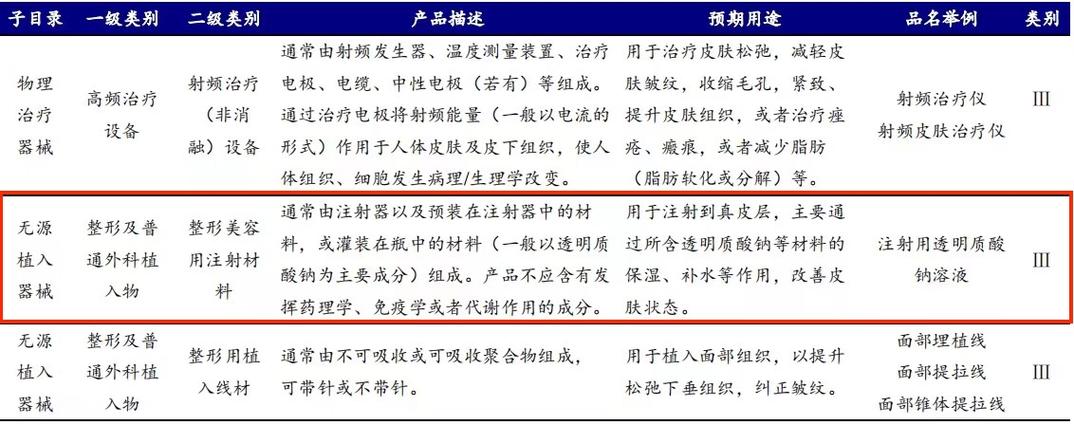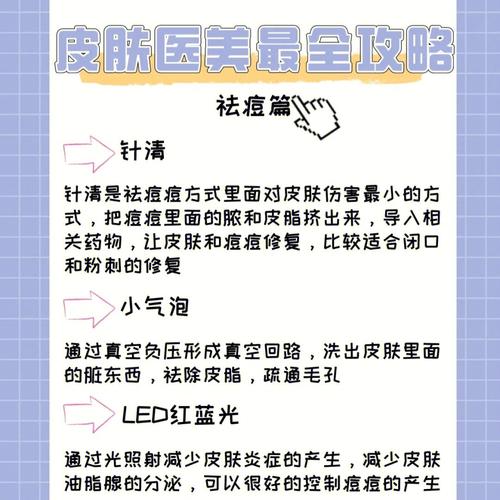文化观潮|刘晓庆:我经常觉得_我好像有200多岁了(演員電影我在)
改革开放后,一批“文化人”出走体制内,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时代,开始重新设计人生下半场。
在大时代下,这些“文化人”的个人命运发生了怎样的转折?作者张英在澎湃·请讲栏目推出“文化观潮”系列口述。讲述“文化人”所经历的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
今天刊发的是演员刘晓庆的口述,讲述她的演艺事业以及人生中的大起大落。

刘晓庆的传奇,也是当代中国传奇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女性,她在“文革”年代生长,经历了反物欲的计划经济,物欲至上的改革年代,从事业到爱情到婚姻,她胆大妄为、我行我素,从下乡知青到文工团演员,从电影明星到加入中国作协,从亿万富姐到阶下囚徒,最后再次回到演艺圈的中心舞台。
本文是作者早前(2012年)对刘晓庆的独家专访。
我的荣誉都是电影给的
中国电影一百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刚(从秦城)出来,正好碰到中国电影百年的纪念,当时我真的是好感谢电影这个行业,给了我很多很多机会和荣誉,我的一生都是电影给的。
在我不同的人生阶段,电影从来没有忘记过我。比如中国电影百年,各种各样的奖励,都有我在里面。我拍的好多电影入选中国电影百年经典片。
比方说老一代电影演员,他们受到时代的制约,可能最红火的时候新中国成立了,原来的演戏道路断掉了,必须改路子,从演城市爱情商业片改为演工农兵电影。
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演员,像谢芳、王晓棠那一代,演到很好年华的时候,就碰到“文化大革命”,然后电影全部停了。“文革”之前毕业的那一批电影学院的优秀学生,浪费和耽误了十年。然后我们这一代演员,就长大了。
我们这代演员,潘虹、徐松子、陈冲等这批演员,很容易,顺顺利利地,拍了几部电影,就红了。这里面,有我们自身的努力,也有改革带给我们的幸运。我的个人成长史,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发展史。
突然就红了
《小花》剧照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没有娱乐这个词汇。电影、文学、艺术是放在文艺战线里头的。从学者、媒体到电影圈里头的人,都把电影当成艺术,视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文革”结束,改革正在酝酿,人们的生活刚刚有一丝松动,日子很单调,人也很单纯。
那时候,明星和影迷之间没有清晰的距离和空间,很多规矩和标准,要在20年以后才确立起来。当我的照片第一次登上《大众电影》封面的时候,人们蜂拥而至,只是为了得到我的签名,读者来信用麻袋装,我根本看不完,云里雾里的感觉遍布我全身。
在拍完《小花》、《婚礼》、《瞧这一家子》后,我发现自己不能出门了。在街头饭馆和朋友一起吃顿饭,楼上楼下和过道里,都围满了闻讯而来的影迷,根本无法下楼。等我在朋友的保护下杀出重围时,身上的衣服被狂热的观众撕烂了,墨镜和帽子早已无影无踪,脚上的鞋子也只剩下一只。
《神秘的大佛》问世后,这部武打片拿下了当年电影票房冠军,电影学者、批评家和媒体认为这个电影不是艺术片,是一部商业电影,批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在当时的文化语境里,扣上了这个帽子,等于彻底否定了这部电影。
我当时认为,观众需要思想性、艺术性都强的好影片,同时也需要一些娱乐性较强的好影片。就把自己的观点写成文章,谈到拍《神秘的大佛》时的思考和辛苦,结果被编辑删得一干二净。
我当时想走演技派演员的道路。我觉得演员是演出来的,就像祝希娟,她不是很漂亮,但是人家就会演,《吴琼花》只有她演最合适,当时我觉得要做这样的演员。接下的《原野》,我在这部电影里演花金子,让我成为了一个成熟的演员。
我渴望演一个真正的女人,我迫切需要一部影片来证实我的道路,我要尽最大的努力证明我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没文化、疯疯癫癫以及浅薄。后来的结果证明,《原野》接对了,让我在表演上真正地开了窍。
当时,《原野》的作者曹禺,看了电影很感动,对我说:“很好,很动人,你演的比我写的还要好!
”
八十年代的个人奋斗
《原野》在电影界内部放映了几场,看电影的专家学者反应十分强烈。中国香港地区、美国、加拿大、意大利都买了这部影片的版权,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原野》获得了“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的荣誉。但受当时清除精神污染背景的影响,《原野》却在国内停映了,不允许在国内发行。
《原野》被禁后,各种猜测、传说不胫而走,最多的说法则是说我们拍了两个版本,其中的一个版本是我拍了床上的裸体镜头。香港的一家杂志登了这些消息,日本的报纸又转载了这个。人们相信谎言比相信真理的程度要深得多,大家都坚信不疑,并且争相传播。
可事实真相是我根本没拍过裸体场面。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使别人相信,也没有人听我的解释。在流言满天飞的日子里,我的“先进工作者”称号在公布名单以后,被北影厂拿掉了。
后来,上海《文汇月刊》的梅朵、余之的提议,让我写一本传记。我在北京西苑饭店开了一间房,拔掉了电话,花三天时间写了《我的路》,发表在1982年6期《文汇月刊》上。
这期杂志被一抢而空,加印了两次,还是供不应求。《文汇报》也开始进行连载。《我的路》发表后没过两周,《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几封读者来信,标题是《我的路通向那里》,并专门发表了编者按,第一句话就定了方向:“《我的路》是一条个人奋斗的路。”
接着《北京日报》、《北京》、《光明日报》、《新民》先后都发表了批评文章,各省市报刊也全文转载了《中国青年报》的读者来信及编者按。许多人在文章里批评我“鼓吹机会,这是宿命论。”有几家省报因转载了《我的路》而受到上级批评,在报纸上做公开检查。
原来想出版《我的路》的7家出版社,也取消了出版计划。我没想到,区区三万字的《我的路》,会引起那么大的麻烦。我怎么也想不通,写篇文章说说自己的心里话有什么错误。
现在回想,《我的路》真正引起反感和轩然大波的原因只有一个:我在三十岁就写了一本自传,让电影界、文艺界、媒体的老同志不满意、生气了,觉得我太狂了,找借口教训下我。
感谢改革开放,最后,随着政治风向的转变,我获得了新生和解放,不仅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还接连演了电影《芙蓉镇》和《红楼梦》。
《芙蓉镇》剧照
艺术重要,生存也很重要
1980年代,除了富起来的个体户外,中国人当时的收入都很低。
我的工资每月只有50元。在农场插队当农民时每月工资27元;参军以后每个月津贴6元,六年后提了干部,工资涨为56元。调到北影,又降为50元。
拍《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的时候,我是北影厂派出的演员,不拿一分钱片酬。这两部电影是属于合拍片,投资方和导演团队来自香港,演员香港、大陆都有。在待遇上实行一国两制。
大陆的演员和工作人员,每顿两个馒头、一根粉肠、一块黑咸菜。香港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大鱼大肉、青菜和香喷喷的白米饭。两分钟前都还一起演戏,两分钟后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后来我很生气,就提出抗议,然后我享受到了香港演员的同等待遇,吃到肉、鱼和米饭。但我要求给剧组的大陆工作人员统一实行香港工作人员的待遇,没有被批准。
作为当时中国最红的女明星,我表面风光,却买不起衣服,住不起宾馆,吃不起好的饭店。无数的应酬、活动在邀请我,请我去演出。但除了拍戏,所有的应酬我一律拒绝,我没有时间,没有心境,何况也没有衣服穿。
那段时间,我也有自己的难处:外婆当时已90岁高龄,父母均体弱多病,妹妹在法国念书,3岁的孩子也在我家里,六口人的开销生活,我都要负责。在外拍电影从来没有酬劳,钱都直接给了北影厂。而生活光凭50元工资,是远远不够的。
当时,拍电影北影厂不给演员提供服装,那时候演员也没有商业赞助。一天,摄制组所在的西苑宾馆来了两个人,请我去河北邯郸演出。他们说演四天二十五场。每场五十元!
一场就是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被吓住了。
当时一些文艺团体的演员参与社会演出,一个演员每场二块钱。我考虑到自己在拍戏,还是回绝了邀请。3天后,这两个人开出了每场150元的价钱。两秒钟后,我点头答应了,跟剧组里的副导演商量,把自己的戏份调到一星期以后,和王洁实、谢莉斯、姜昆、李文华、唐杰忠、苏小明等北京文艺界的人,一起坐火车去了邯郸演出。
我表演唱歌,150元!
一首歌一共不到十五句,一句十元钱!
钱太容易挣了。第一次走穴,就拿到了3700元人民币,这在1983年的中国,可是一笔巨款。
因为天南地北的走穴演出,我的歌唱水平日臻成熟,录了五盒歌唱磁带,其中《刘晓庆的歌》还获得了太平洋影音公司颁发的“云雀奖”。
我记忆里最长的一次演出“走穴”,创下了中国演出市场的最高记录,每天至少六场,多的时候八场,一共连演了四十七天。演出一场紧接一场,演员连上厕所的工夫都没有。
靠着演出的原始积累,我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为以后的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仅买了车、房,还把四川的亲人都接到了北京。
1995年,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宣布下海经商,当老板拍起了电视剧,出品和拍摄了《火烧阿房宫》、《逃之恋》、《火凤凰》等电视连续剧。
做生意和做演员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做生意是理性思维,做演员是感性思维,当时我非常年轻,又是一个女的,在生意场坐都坐不稳,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打下了一个晓庆王国。
回首当年的劫难
当时《福布斯》杂志中国百名富豪榜刚刚开始,第一年我第42位,本来我很引以为骄傲的,第二期排名第43位,第三期我就被抓进去了。
当我在秦城监狱的时候,觉得很不好,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后来心反而特别宁静和坚定,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因为我本来就没有钱、没有名,只不过是到名利场上逛了一圈,再回到原处。
秦城没有什么事儿干。结果我就跑步、看书、学英文。
在秦城的那些日子,看到电视里放的电影,我就想,可能我一生都不会再演戏了。因为我进秦城的时候,已经不年轻了。我是1955年出生的,当时45岁了,对演员来说,过了演戏的黄金时代了。
按道理说,我名义下的那些公司,我根本就没有参与过运营管理,这些公司有直接的总经理、经理人负责,它在经营上和所有的公司一样,可能有一些问题。当时国家的税法不健全,法律不健全,如果按照对付我们的标准,基本上家家公司都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曾经人家说我是影视圈的第一老板。可见我企业做得还是很成功的,不然怎么会有税的问题。其实我主要是做房地产,涉及各个领域,加湿器、服装、化妆品,影视公司是最后才成立的,就是这个小公司,有税的问题。
当时我就觉得,我从另外一个领域,证明了我的才华。这个税案并不是说我做生意不成功,恰恰证明我是成功的,因为有收入才上税嘛,一个注册只有50万的小公司,是我公司里最小的一个公司。
我名义下20多家公司,他们就查了其中最小的文化影视公司。作为我个人,是一分钱的问题都没有。我只是被他们请到看守所,强制配合接受他们的调查。
出来以后,发现自己欠了好多钱,我也没慌。现在回想,出来的那段时间,恰恰是我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刻。这段经历,我觉得确实是不可多得的财富。但当时在秦城里面不会这么想。
我做到了“咸鱼翻身”
一般来说,一个演员,有我这样的经历以后,艺术道路是要夭折的。我刚从秦城监狱出来,很多人都觉得我完了,有的说是咸鱼浮水,一看死定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拍了好多戏、电影,仍然受到大家的欢迎,活跃在影视战线,我觉得不要说别人,我自己都觉得是一个奇迹。
演员这个职业是我可以掌控的,也是让我心安理得的。我一心一意做演员,在很短的时间里,接拍了《281封信》、《永乐英雄儿女传》、《大宋碑歌》、《谁主沉浮》等近千集电视连续剧,回到了影视圈。
那会儿我欠债累累,就是跑码头嘛,只要给我钱,我什么戏都演。朋友们都特别理解,他们都知道我缺钱。我拍了好多电视剧,培养了不少年轻观众。过去电影的观众,也没有丧失。作为一个女演员,在创造不同的艺术形象上,我还有很多可能性。
我还打算写第三本传记。出传记也是为了以后人家拍我的自传电影方便,现在已经有好多家公司联系我,想拍我的传记片。至少我活着的时候是不同意的,但死了以后就不好说了。我的野史又特别多,我想还原真实的自己。
《我的路》、《我这八年》以后十几年里,我没写过一个字。那个媒体上的刘晓庆,张牙舞爪,咄咄逼人,叱咤风云的人,根本就不是我。说我和每一个我所合作的导演睡觉、生活作风不正派;偷税漏税,离婚,打观众、同吵架……,都是瞎编的八卦,不是真实的,我看那个刘晓庆,我觉得都是在说另外一个人,不是我自己。
我有过很狂的时候,在上世纪80年代,觉得自己名扬天下、不可一世、目空一切,见到就打架,恶名远扬。现在我的个性还是很张扬,但在公众场合收敛多了,不会再那么锋芒毕露,伤到别人就不好了。而且现在影视圈这山还有那山高,人多,竞争激烈,不像当年,就那么几个人。
我把第三本书命名为《我的N次危机》,因为尼克松写了一本书叫《我的六次危机》,后来我一想我才不止六次,太多次了,这本书是肯定要写的。
初中就去农村当知青
我受父母影响比较大,对别人的优点特别敏感。我父亲是一个医学教授,性格很温和,我的母亲是教育学院毕业的,是四川体育学院附中的校长,性格非常好强,对我和妹妹要求特别高。
我们家里只有我和我妹妹,如果我们在学校,比方说拿回来的成绩单,小学不是双百分,是99,我妈妈脸就垮下来了。我妹妹都是双百,我经常还会因为一个标点符号错了,只拿99分。所以,我们家里是慈父严母。
由于我母亲的教育,我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开始看长篇小说,比较早熟。
后来,差不多初中毕业,我们下乡去当知青。初中,我读的是四川音乐学院附中,初中班实际上招了我们这一班,下面还有一班。
读完了初二,一半学生分到边远地区做普通农民,一半学生去少数民族地区做农场工人,每个月29.5元,带薪劳动。因为拿工资,所以干的活是全天的工,非常辛苦。我就记得,当时玉米叶子边缘有很多尖齿,我在摘花粉的时候,玉米叶子尖从我的眼球当中划过,整个世界就变成一片血红,我想眼睛肯定完了,而且根本没有人帮忙,因为谁都有一堆活要干,都是一个人管两亩地。
当时我在地里蹲了好长时间,眼睛很疼,流了很多泪,幸好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我当时指望当地的男农民来帮我干活,这样我就嫁给他,谁对我好我就嫁给他,结果没有。因为当地农民,不会看上我们这种娇气包,他们都喜欢身强力壮的,能够干活,拿600个工分的女劳力。农村妇女很辛苦,下地干活,喂猪、做饭很能干,然后还要照顾家庭。像我们这种娇气包,干活根本就不行,花拳秀腿,没有什么用。
因为我父亲是中医,是体育学院保健系主任,我跟父亲学过针灸,当地人有中暑晕倒的,我有时候就给他治一下。后来声名传出去了,经常有人找我看病。人家来找我,我就翻书看,你哪儿疼,应该是扎哪儿。后来因为表现好,我还得了一个农场的“五好工人奖”。现在回想,我拿过那么多奖,除了杰出华人奖,就是那次“五好工人奖”印象最好了。
扬琴让我当了文艺兵
在农村干活的那段时间,我没有放弃希望。每天晚上,我会望着星空,觉得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颗星星。我带着扬琴,我的专业成绩太优秀了,我不能丢我的专业,每天晚上,我就在操场上坚持练习扬琴。自己打扬琴自己唱歌,好多当地农民来听。后来修襄渝铁路,成立了一个宣传队,我在宣传队当队长,在修铁路施工现场演出。后来,军队普及样板戏,到处招演员,就听说我这个农场,有个人是音乐学院附中毕业的,会弹扬琴唱歌。然后他们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当兵?
农场这边不放人,怎么办?他们问,你敢不敢跑?我说怎么跑?他给我留了一个名字,让我去达县军分区找他。当天晚上,我和宣传队的人吃了一顿铁路上那种民工饭。第二天,我带着扬琴,就坐了一个货车,到了达县军分区。
我本来在学校成绩就挺优秀的,主科是扬琴,钢琴和声乐是副科,舞蹈也很突出。十八般武艺一使,就把部队面试的工作人员,给震住了,当天我就穿了军装,就这样当了兵。当时我父母还是牛鬼蛇神被批斗。
当兵很辛苦,当兵第二天就拉练,一百多里路,走到后来都睡着了。经常是紧急集合,两分钟,你就要把所有包打上,要到外面去站着。我也是一个好强的人。所以我当了十年兵,这种磨难,使得我真的觉得是无坚不摧,觉得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所以才养成我现在这种性格。
在军队,我后来又被分配到图书室管图书,看了好多传记,比如《第三帝国的兴旺》、《巴顿将军传》,《拿坡仑战役》,当时看了很多这些书,对我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后来,我成为了部队宣传队队长,工作弄得也挺火的,是样板,然后从达县分军区调到四川省军区,从四川省军区调到成都军区的战旗话剧团,前前后后调了七八个单位,最后到了北京,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
每个人的人生里,有很多小的机会。你只要抓住很多小的机会,大的机会就会到来。我当时不知道,我将来能够变成电影明星。当时根本没有想这个事儿,就是一步步,工作做得最好,把自己的路走好。人生在不同阶段,到了一定程度我就对自己说,你应该做新的事了。
生活中,我本人脾气是很好的,大家都不会相信。性格属于那种俯首甘为孺子牛,对朋友对家庭、亲友都很好。我只是在工作上特别严格,有的时候很尖锐,没有办法,就好比一个医生要治病救人,在开刀的时候,助手要是叉子、剪刀拿得不对,医生会一下子甩出去,因为要争分夺秒救人嘛。我们拍戏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情况。
在影视圈里,我不仅不潜规则,我还帮了好多人。当今的好多大腕,其实都是我发现,我先提携他们,帮助他们的。
经常有人问我多大,其实每个人都知道我多大。我经常觉得,我好像有200多岁了,因为我已经活过好多个不同的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