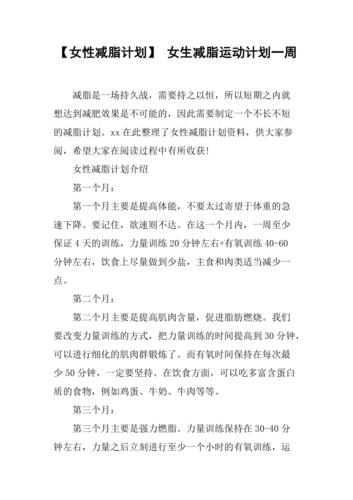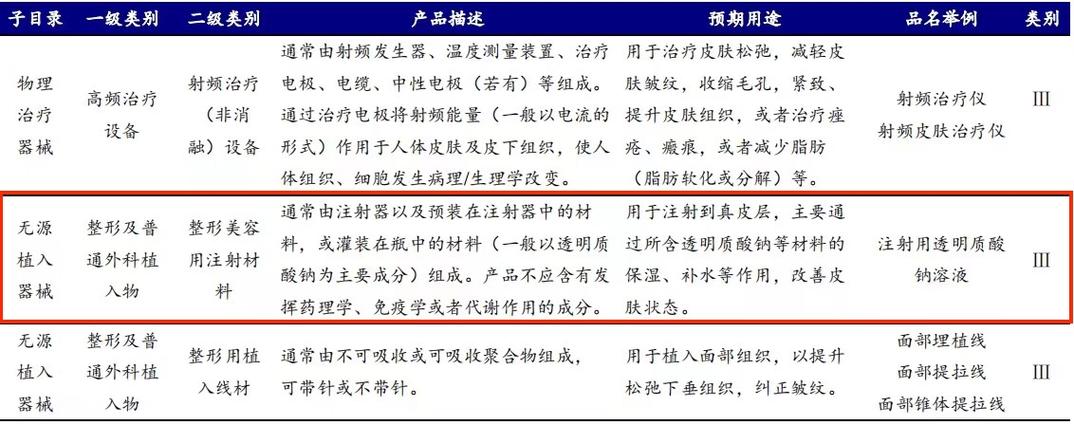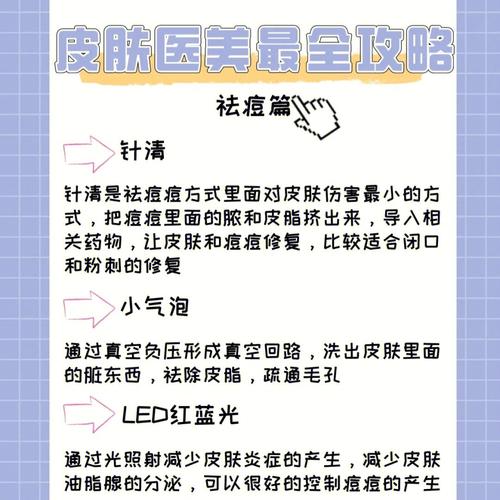曹军庆:在美容院楼上(筆記本素素睡美人)
楼房背面与正面宛如两重天,新城区都是匆促建成的。
是用擀面杖建成的。
像面团那样没完没了地往外抻拉。
拓展马路,先把街区拉出去,再向四面八方延伸。
这就有了新街,漫长的新街。
马路那面车水马龙店面密集。
后面,背对着的那一侧则是荒野之地。
菜畦、土坑、水塘以及无主坟堆。
城市之光照临此处,高楼大厦将立起来。
红绿灯、商场、吊塔、有轨电车和地铁也将分布在这里。
早晚会这样,其他城区提供了现成的先例。
城市就像张开的嘴,先把肉吞进去,随后再吐出骨头。
土地就是那一片片的肉。
至于骨头,可以想象从土地里剥离出来的东西。
这种剥离有时候需要年份,有时候不需要。
年份骨头。
被嚼过的渣滓。
城市之胃就在我们头顶或眼前蠕动。
这里是城乡交接处,是前面说到的新城。
焦家有栋三层小楼。
很早就在这里了,那时候还是农村。
旧房,寻常住所。
为了做生意,重新装修了房子。
只有三楼没有装修,三楼是他们焦家人自己挤着住的地方。
做生意的人是焦家小女儿焦美丽,她不让家人从她的店铺经过。
不能打扰客人。
他们只能从楼房背面,贴着墙壁从露天楼梯攀爬上去。
这架楼梯是后来施工加上去的。
钢筋焊接在墙上,加上护栏,再铺上水泥板。
弯曲、狭窄、陡峭。
焦美丽把工钱压得很低,施工方不得不偷工减料,不得不使用低劣材质。
这使得楼梯看上去锈迹斑斑,风雨飘摇。
远远望去,就像扭曲着贴在墙壁上的蚯蚓,丑陋不堪。
而正面的一楼和二楼,因为是门脸房,则显得格外光鲜明亮。
焦美丽开着美容院,名字叫睡美人。
晚上,睡美人美容院的灯箱广告在空旷的夜空照射到很远处,几条街外都能看到。
广告图片和言词极具诱惑。
很多女人开车而来。
她们为自己关于瘦身或整容的想象所折磨,甘愿在此一掷千金。
焦美丽的生意火爆一时。
美容院内房间宽敞,一楼和二楼上下有内楼梯,往返便利。
这是经过改装的原来的楼梯。
原来也能通到三楼,但是通道在二楼被砌死。
门里进进出出的,都是各色美女艳妇。
她们并不知道楼房背面还有贫民窟似的楼梯,摇摇欲坠,也不知道有人从那里上到三楼。

这天,有个瘸子登上了这架楼梯。
不远处,在一棵秃树下面老袁正忙着。
老袁——他的本名叫袁克隆——用帆布搭了个棚子。
棚子旁边是没有水的池塘,底部早已干涸。
袁克隆是个捡破烂的老头,他在此处所待的时间,比焦家的这栋房子年代更久远。
捡来的垃圾需要分类。
于是,他在板结龟裂的池塘底部捆扎挑拣好了的旧报纸。
一抬头,刚好看到瘸子往上爬。
老袁不能确定他是瘸子,还用手在额头上搭着凉棚仔细辨认。
的确是瘸子。
他拄着木棍,敲打着踏板往上走。
另一只手还得死死拉住护栏。
他走得很困难,歪歪倒倒,趔趔趄趄,老袁有几次担心他会摔下来。
他停下来擦汗,顺便喘口气,这时也掉头往外看,他也看到了袁克隆。
可能是想看得更清楚,他也拿手在额头那儿搭凉棚。
“这个捡破烂的麻木,还没死啊。
”
在他认出老袁的同时,老袁也认出了他。
“他不就是焦家的儿子吗?”焦家唯一的儿子焦光忠。
焦光忠前面有个姐姐,姐姐前面还有个姐姐,她们是他的大姐和二姐。
后面是妹妹焦美丽。
焦美丽大约是焦家仅有的经济支柱,或者不如说是仅有的经济来源。
更刻薄一点儿说,正是她的睡美人养着焦家全家人。
没有她全家都将衣食无着。
比如她要养着大姐大姐夫二姐二姐夫。
他们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下岗职工。
焦美丽为他们支付生活费,还要适当支付部分医疗费。
他们的身体都不好,大姐夫脑瘤,二姐夫前列腺有问题。
大姐切除了乳房,二姐切除了子宫。
下岗职工所有的痛苦,似乎都能从他们身上找到例证。
而且不是孤证,姐姐和姐夫永远在相互印证。
他们就像跟命运赛跑那样,身体的溃败谁也不甘落后。
但是谁跑到前面都会羞愧,因为那意味着自己需要花更多的钱,因此焦躁并厌世。
还有两个老人——焦父焦母都还活着,焦美丽养着他们毫无怨言,他们是这所房子事实上的主人。
父母是房主,睡美人美容院占着他们的地盘。
如果是别人的房子,另外还要交一大笔租金。
现在至少省下了这笔钱。
大姐的两个女儿都是睡美人的员工。
二姐同样有两个女儿,一个也在睡美人,另一个在广东打工。
二姐最近老在找焦美丽,希望她能接收在广东打工的女儿。
她已经给她打过电话,要她回来发展。
麻木袁克隆放下搭在额上的手,嘴角浮现不常见的笑容。
他此时的笑容,挂在焦家楼房外壁上的焦光忠根本无法看到。
焦光忠回到家就是个瘸子,他左腿断了。
听说是吸毒时,为逃避警察抓捕摔断的。
伤处夹着护板,缠了绷带。
但凡手头有点钱,但凡日子还过得下去,他是不会回来的。
他长时间漂泊在外。
吸毒者好像都是这个样子。
孤独者,也是群居者。
糟糕时在桥洞或公园草地上过夜,有了钱就住酒店。
他们有相同的气味和眼神,既独来独往又呼朋唤友。
“毒友”各自蛰伏在不起眼的角落里。
他们是城市牙缝里的残渣。
这类残留物有时候被牙刷牙线清理掉,有时候顽固地依附藏匿在褶皱里。
他们在藏身处腐败,发出变质的臭味。
在城市的口腔里,他们等待自己的命运。
如同秋树的叶子,寒冬等在不远处。
但是焦光忠回家了。
这是个意外,是个奇迹。
他好多年都没回来过,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回来的。
他是焦家的祸乱之源,他不需要这个家,这个家也不需要他。
可能是养伤的缘故,不把腿伤养好他会死在外面。
最倒霉的时候,最无处可去的时候,还是会想到家。
所以,他拄着一根粗木棍又回来了。
不回家我能去哪里?这几乎不是领悟,而是经历了若干次的事实。
落难之时唯一能收留自己的地方不就是家吗?
粗木棍敲打着护栏上的锈钢筋条,发出哐啷哐啷的脆响。
家里人想,他戳根棍子是怎么歪歪倒倒走上来的呢?
这里住着一大家子人,住着焦父焦母大姐大姐夫二姐二姐夫。
除了焦美丽和姐夫们的女儿,其他人都住在这里,一共六个人。
大姐夫和二姐夫轮流买菜做饭。
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抱怨、看电视、吃药打针和偶尔下去遛弯儿。
焦光忠是那个突然多出来的人。
他被安排在紧邻洗手间的杂物间里。
那里从前不住人,是摆放杂物的地方。
焦光忠住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奇怪物品,比如焦父焦母扔掉的结婚证。
这个国家早年的结婚证,现在看起来就像是珍贵文物。
但是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知道结婚证是被谁扔掉的。
什么时候扔掉的?另一个人知不知道他们的结婚证被对方扔掉了?在满是灰尘的杂物间里,焦光忠从废物中发现了不止一样诸如此类的秘密。
其他人对他都很冷淡,很明显,这些人不欢迎他回家。
对他有敌意,不信任他。
他的劣迹不限于吸毒,还包括偷窃。
他是个高明的扒手,从小学时起就精于扒窃之道。
更让他们费解的是,就连家里人他也多次偷过。
大姐夫曾经说过:“小偷如果吸毒,就会无差别偷窃。
”
二姐夫表示同意:“他才不在乎你是外人还是家里人。
”
因此,家里的风声忽然间收紧了。
每个人都提高了警戒等级。
所有可以上锁的地方都被锁上了。
尤其是现金,收藏严密。
焦父问焦光忠:“你回来干什么?”
父亲比上次见到时苍老多了,他的脸庞像烙煳了的玉米饼。
焦光忠答道:“我得找个地方养伤。
”
“你怎么就把腿摔断了呢?”
“警察追我,我从三楼窗口跳下去。
窗外有棵树,我落在树枝上弹跳了一下,然后才落到地上。
那根树枝救了我一命。
如果没有树,我摔断的就不是腿,肯定就没命了。
”
父与子说话时,焦母也在。
她眼神不好,瞳仁浑浊。
“你总是这种时候就回来了,没办法的时候,没着落的时候你就回来。
好的时候你从不回来。
”
“他哪有好的时候。
”焦父抢白道。
“这是我的家。
”焦光忠说。
“我养好伤再也不出去了。
”他又说,“也不再吸了。
”他望着焦父焦母,他的姐姐和姐夫全都缩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
他们正在阅读药品包装盒上面的说明文字,同时也在竖着耳朵倾听客厅里的谈话。
“这话你说过好多遍了。
”
“谁都不信,你自己也不会相信。
”
“我不吸了,去找份工作。
”
“你是想让我们开心吗?”焦父说。
“他总是这样,为了让我们收留他,他就发这种誓。
”焦母折回自己的房间,她说,“他在耍花招,哄骗我们。
”
“你戒得了吗?”
“我戒得了。
”
焦母对焦父说:“他戒不了。
”
焦父叹了口气:“我也这么想。
”
腿伤一天好过一天,焦光忠想哪天能扔掉粗木棍自行走路就好了。
他在家待不住,有空就下楼。
他去找老袁,坐在老袁的帆布棚子里。
坐上一两个小时。
老袁若在,他就坐那儿跟他聊天。
老袁若不在,捡垃圾去了,他也在那,就孤零零地单独待着,他愿意。
帆布棚子敞开着,里面堆满各种垃圾。
老袁的床铺在棚子角落,跟垃圾混在一起。
猛一看,老袁就睡在垃圾里。
再仔细分辨,那一块儿大体上还是能找到某个床的模样。
长期躺过的印迹,看着和一张床铺差不多。
焦光忠觉得待在这里比待在家里更叫他安心。
他老早就认得老袁,上学时就认得他了。
大家都叫他麻木,这一带没人不知道他的名号。
“有破烂吗?叫麻木来收吧。
”
可能只有焦光忠知道他叫袁克隆,是他自己告诉他的。
那天,老袁扯着焦光忠的书包带子,附在他耳边对他说:“我不叫麻木,我有名字,我本名叫袁克隆。
”
焦光忠闻到了一股烧酒味道,还是清晨,清晨麻木就开始喝酒吗?他为什么要告诉我?告诉一个正要去上学的小学生?“这名儿好,比麻木好。
”
“你可以叫我老袁。
”老袁神秘地说,然后转身走了。
从那时起,焦光忠从没忘记老袁的名字。
“你还记不记得,你的名字是你自己告诉我的?”
老袁茫然地看着他,他又在捆扎垃圾。
“你告诉我你叫袁克隆。
”
老袁摇着头,“不是。
”
“你让我叫你老袁。
”
还是摇头,老袁说:“我是麻木。
”
老袁木讷,嘴拙,听力也不好。
这么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话很困难。
要么是他的记忆出了毛病,要么是他曾经在喝了酒之后随意给自己起了个名字。
或者就像捡垃圾一样,他无意间在哪里听到了一个别致的名字,便在幻觉中安在自己头上。
比如刚好那天他听到谁叫袁克隆,这名儿不错,他得捡回来。
又刚好碰到焦光忠,他就告诉他了。
焦光忠不想在这上面纠缠。
他说:“你不嫌弃我吗?”
“不嫌弃。
”
“我也不嫌弃你。
”焦光忠说,“我们是朋友吗?”
“朋友。
”
“那你不要再捆垃圾了,这样捆老也捆不完,我们喝酒吧。
”
焦光忠从怀里掏出半瓶酒,不是正好半瓶,是小半瓶。
老袁手搭凉棚看了看远方,他在看什么?随后他在床头掏摸了好半天,摸出一小袋花生米。
“你这儿倒是有宝贝。
”
老袁诡秘地笑着,一副极有城府的样子。
“还有烟。
”焦光忠接着掏出烟来了,不是烟盒装着的烟,是散烟。
用纸张包着的若干根散烟,不同牌子的烟混着。
焦光忠挑了根好点的烟递给老袁,“你抽这个。
”
小半瓶酒没多久就喝光了,焦光忠又掏出小半瓶酒。
他怀中就像藏着个百宝箱。
老袁脸喝得通红,焦光忠脸喝得煞白。
老袁指着他的脸,又指着自己的脸,说:“酒鬼。
”
焦光忠拍了拍自己的伤腿,“我跟你说说悄悄话。
”
老袁领会到他的意图,把头伸过去,耳朵递到他嘴边。
“酒鬼也好麻木也好,我长着个鬼的鼻子呢。
你知道吗?我的鼻子跟鬼一样。
随便一闻就能闻到钱的味道。
你这儿有钱啊老袁。
嗯嗯,我只要再闻闻就能闻到钱的位置。
”
“我没钱。
”老袁惊慌失措地望着他的床铺。
“开个玩笑啊,我也知道你没钱。
”焦光忠揪了揪鼻子,仿佛想把鼻子从脸上拔掉,如同鼻子是他脸上的酒瓶塞子,只要拔掉,就有酒涌出来,“你知道我这酒是从哪里来的吗?还有烟,这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偷来的。
”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老袁,你这个麻木。
”
“嘿嘿!
”
“可是,这次不是偷来的,不是。
”焦光忠摇晃着手指头。
“烟是我爹给我的,酒是我妈给我的。
他们夜里总要上洗手间,瞅着空,我爹就把烟从门缝里塞进来了。
我妈也是,从门缝里把酒给塞进来了。
”
“他们?”
“听脚步声我就能分清楚。
知道给我烟的是我爹,给我酒的是我妈。
”
“我信。
”
“他们分别给我东西,偷偷摸摸给。
但是他们不让对方知道,一个人生怕另一个人知道自己在给我东西。
”
焦美丽回来过几次,她回来看望焦光忠。
“哥你回来了就好,我一直盼着你回来呢,你回来了就不要再出去了。
”姐夫姐姐们都很佩服焦美丽,她说话总是滴水不漏。
她还许诺,要把这边的楼梯重新修一修,“要不然,再新修一架楼梯吧。
也花不了多少钱,旧楼梯走着太危险了。
”
“我以后就在家里。
”焦光忠保证说。
“那就好。
”
“我去找份工作,粗活重活都行。
”
这话他跟焦父也说过。
“伤好了再说。
”焦美丽咧着嘴角笑,哥哥真贴心啊!
没过几天,事情终究发生了。
不是意外,要发生的事总会发生。
焦美丽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在三楼,在客厅茶几上不翼而飞。
全家人找破脑袋也没找到。
笔记本不能碰,都知道那是不能碰的东西,焦美丽看得比眼珠子还重要。
前天吧,就是前天,她来看望哥哥。
两人愉快地聊了会儿,结果笔记本落这里了。
今天她要用,上来拿,却发现已经没有了。
焦光忠也不在。
他去了哪里?他在干什么?所有人都面面相觑。
“我真不想怀疑他。
”焦美丽眼泪都快出来了。
这时,焦光忠刚好拄着那根粗木棍子哐啷哐啷上楼来。
他脸色煞白,煞白得就像来自阴间。
他的脸之所以煞白是刚在下面跟麻木喝过酒,可是其他人不知道这回事,也不会这样想。
“哥你出去了?”焦美丽尽量把话说得平和一些,在她发问时,焦父焦母和姐姐姐夫们齐刷刷回房去了。
他们半掩上门,只留着很小的门缝。
“出去了。
”
“你去了哪里?”
“哪里也没去,就在楼下。
”
“就在楼下吗?”
“就在楼下,麻木那里。
”
“麻木是谁?”
“老袁,袁克隆。
”
焦美丽望着焦光忠的眼睛,它们像两枚钉子死死钉在他煞白的脸上。
我不能再这样问下去,否则会被他牵着鼻子走,永远一无所获。
扯什么麻木,我必须直截了当。
“你出去卖了什么东西吗?然后又买了什么?”焦美丽目光如炬,她仍然是在苦口婆心地问着,不是审讯。
不是审讯,妹妹没有审讯我。
审讯我见过太多了,这回不是。
焦光忠这样想,心里会好受些。
“我没有卖什么,也没有买什么。
”
“可是我的笔记本不见了,我前天拿回来的,就放在茶几上。
以前也放那里。
怎么就会不见了呢?这个家谁会拿我的笔记本?哥你替我想想,谁会拿?”
“你怀疑我是吧?但不是我。
”
“那会是谁?”
“不是我。
”
“哥我告诉你,不是笔记本的问题,也不是钱的问题。
里面有资料,很重要的资料。
有财务信息,还有顾客的个人隐私。
她们不允许这些东西流出去。
”焦美丽蹲着,蹲在地上,蹲在哥哥伤腿那儿,“你明白吗哥,这个家里你什么都可以偷,就是不能偷我的笔记本。
”
“我没偷。
”
“个人隐私,哥你明白吗?那些女人谁也不愿意她们的隐私流出去。
发生这种事,我的饭碗就砸了,彻底砸了。
再也无法挽回,你明白吗哥?睡美人不是我一个人的饭碗,是全家人的饭碗。
”
她抚摸着哥哥的伤腿,就像丢失的笔记本就藏在那里面,就像她所提到的那些隐私就在那里面。
刚才在老袁那里,焦光忠也拍过伤腿,他拍着那里和老袁说悄悄话。
“我和那些隐私没关系。
”
“你要承认哥,你不能不承认。
”
她还是认为是我偷的,并非栽赃,是认定。
推理性认定。
如果我是她,又能怎么想?还会是谁?可不是我,我没偷。
焦光忠很愤怒,他不是被激怒的,而是因为绝望而愤怒。
他从来没有如此绝望过。
于是,焦光忠冷笑着说:“我没偷,别说谁的隐私,就算笔记本里全是国家秘密又怎样。
不能因为重要不能因为神秘,就赖上我是吧?”
“我容易吗?”焦美丽突然说出这种话,“我一个人养活一大家子人容易吗?你看看他们,他们也是你的家人。
没有我,他们能活下去吗?”
在那几扇门后面,他们寂然无声。
他们在想什么?
焦光忠一直在回想,回想这几天的所有情形。
他闭着眼睛,现在他想到了钱素素。
钱素素是他从前的“毒友”,昨天下午曾短暂来访过。
他回家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她耳中,她表示一定要登门拜访。
来之前,她打电话说:“老朋友啊许久没见,听说你还伤了腿,我一定要上门来问候你。
”
“谢谢你的关心,不用看我,我还是老样子。
”
“你的腿没问题吧?”
“没问题,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
“还是想当面看看你,你不介意吧?”
“不劳你动身了,电话里聊聊也是一样。
”
焦光忠反复拒绝钱素素,她还是来了。
忽然间就在焦家现身了,这些人习惯于不请自到。
刚进门,钱素素就高声说道:“不要我看你呀,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既然如此,我倒还想让你看看我呀。
送上门来给你看,难道你不想看到我吗?”
钱素素咯咯笑着说,她努力想要笑得更暧昧一些。
她这么说有原因,老早以前他们之间有过一段非同一般的关系。
那还在他们都是正常人的时候。
正常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反正有过那种时候。
他爱她,只是她没有应允他。
她那时候是个清高的女子,牙齿干净,额头发亮,头发也没有脱落。
她此时状态不好,非常不好。
她为什么要跑过来呢?像个病入膏肓的临终病人。
她肤色暗黑,两只脚抬不起来,每一步都像是在空中飘浮。
说话经常停顿,不停地喘息。
她像探视病人那样握了握焦光忠的手,这才落座。
“你们家楼梯很危险。
”钱素素说。
“我没觉得,我们一家人就生活在这上面。
从那里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倒是方便。
”焦光忠双手交叠着搁在肚腹上。
“那当然,那当然。
”钱素素赶紧附和,“倒是方便。
”
“我瘸着腿也能上来。
”
“还疼吗?”钱素素摸了摸焦光忠的伤腿,“下面是睡美人,这里,你们住的地方算是睡美人上面的阁楼吗?”
“不是阁楼,是一层楼,整整一层楼哇,就是三楼。
”
“哦哦,是这样,我还以为只是阁楼。
以为是孤岛,是悬浮在繁华美容院之上的一座孤岛呢。
这样想有意思吗?”
说到这里,钱素素又一次咯咯咯地笑。
在他们都还正常的时候,钱素素热衷于写诗。
阁楼、孤岛是她写诗时经常用到的词语。
“你把我带回到了你写诗的年代。
”
“我写过诗吗?”
“写过。
”
“楼梯虽然危险,但是太有趣了。
走在上面吱吱嘎嘎,吱吱嘎嘎。
”
“我可以告诉你,美容院里面的楼梯是很好的楼梯。
我们的睡美人有内楼梯,就像高档酒店的楼梯那样。
”
“我知道,我知道。
光忠,我的日子可能不多了。
”
“别这么说,我们这一行的人都爱这么说。
”
“也是,我们这一行的人都爱这么说,都爱危言耸听。
”
“不是危言耸听。
”
“不是危言耸听,有些人说着说着就没了。
”
“你不能这么想。
”
“可是我手上没‘粮食’,很久很久都没‘粮食’了。
光忠你能借我点钱吗?刚见面就跟你借钱真不好意思,可我没别的办法。
有别的办法我也不会来找你。
你随便借我点好吧,能借多少借多少。
我不在乎多少,只要能借我点就好。
”
钱素素边说边吞咽口水,焦光忠知道她所说的“粮食”指什么。
原来她不是来探视他,也不是来问候他。
她是来借钱的,她走投无路了。
“我没钱,这种情况我怎么可能有钱。
”焦光忠很抱歉,他确实没钱。
“真不给我面子。
”
“这不是面子的事儿。
”
钱素素说:“好吧,那我走了。
”
钱素素就那样走了。
焦光忠想到这里,终于明白了。
一定是她走过客厅时顺手牵羊拎走了笔记本电脑。
他根本没注意,想不到钱素素在扒窃高手眼皮子底下居然也能偷走东西。
如此说来,焦美丽并没有冤枉他。
他有什么理由愤怒?钱素素偷的和他偷的又有什么区别。
事实已经这样子了,难道还不够吗?
焦光忠打电话找到钱素素。
电话打通了,他先不开口,等着她说话。
钱素素软和和地说:“光忠,你还记得给我打个电话呀,难得难得。
”
“还没死啊你,你不是说你日子不多了吗?”
“快了快了,指不定哪天呢。
你干吗这么性急!
”
“还不是因为你干的好事,你在哪里?”
“先不着急说我在哪里,说你吧,你还困在那间阁楼上吗?”
“为什么你总说那是阁楼?好吧好吧,我还在阁楼上。
”
“或者你还在孤岛上?美容院楼上的孤岛啊,你还在上面吗?”
“好吧好吧,也还在孤岛上。
”
焦光忠明白,这时候得顺着她说话。
若不顺着她,若跟她拧着说话的话,她随时会把电话挂掉。
钱素素在笑,笑声变了。
不再咯咯地干笑,而是咕咕地笑,有些湿润。
她笑得像鸽子。
不是一只鸽子,而是一群鸽子。
一群鸽子咕咕咕。
钱素素很少这样发笑,她笑得很有感染力,笑得无拘无束。
“我正嗨着呢,你要不要也来搞?”
“搞什么,还好意思嗨?你是不是偷了我们家笔记本?”
钱素素继续咕咕笑,笑了老半天。
“那不是偷那是顺,那也不是顺,那是借。
没那笔记本,我现在还嗨不起来呢。
”
她在嗨,还用说吗?听到她的笑声,他就知道她在嗨。
“少他妈扯!
赶紧还我。
”
“怎么还你?还笔记本吗?你也太幼稚了吧,你是毛孩子吗?我不是正在嗨吗?正在嗨你听不懂吗?”
“你卖了?”
“卖了卖了,早卖了。
不卖哪有钱嗨呀!
”
“好吧好吧。
”焦光忠告诫自己要冷静。
我得知道她卖到哪里了。
“嗨吧,我只是想知道你卖给谁了,我说的是笔记本。
”
“你说的是笔记本,我当然知道你说的是笔记本。
”钱素素咕咕笑着,“你好啰唆,你真啰唆。
笔记本卖给老开了,老开你也认识的,我们的老熟人。
你应该记得他,以前我们偷回来的东西都得卖给他。
”
记得记得,焦光忠感到恶心,想吐,“老开给你多少钱?”
“老开你还不知道哇,他抠得很,只给了八百。
”
“八百吗?你跟他说,我要买回来。
”
“我没听错吧?你要花八百块钱再把笔记本买回来?为什么?那破笔记本值吗?你自己找老开吧,我才不管这事,你跟他说好了。
”
焦光忠又去找老开。
老开听说后,声称笔记本还在,还没销售出去。
不过,他要价一千块。
老开说:“你要买回那个笔记本吗?这么说,是你的笔记本?我们也算是兄弟吧,我们之间的事好说好说。
一千吧,一千块钱我给你。
”
“可是钱素素说,她卖给你是八百块钱。
”
“没错没错,她卖给我是八百块钱。
”老开说,“可是我不能也八百块钱再卖给你呀,我要是再八百块钱卖你,岂不是个大傻瓜!
”
老开在销赃这个圈子里是说一不二的人物。
到哪里去弄一千块钱呢?我要尽快把笔记本赎回来。
老开有众多耳目,一旦惊动了他,就会起疑心。
我后悔没弄到钱就跟他讲了。
他会不会去动那部笔记本?他会查阅里面的资料并把它拷下来吗?把资料卖给需要的人,或是以这些资料要挟我出更高的价钱?我能想到的事情老开能做出来,我想不到的事情他也能做出来。
我得火速弄到钱,一千块钱,可是去哪里弄?
焦光忠开始焦躁,同时他还难过。
他现在唯一的念想是把焦美丽的笔记本还给她。
就像笼子里的老鼠,都已经被关起来了,还有人拿着烧红的钳子,伸进笼子里来夹它。
夹它的人是在取笑它,娱乐它。
他在玩耍。
拿钳子的人发出嘲讽的笑声,高大的身影横亘在远方。
焦光忠此时就是那只老鼠。
他需要钱,需要赎回赃物。
那才是他的避难所,他的逃逸之路。
只有拿到一千块钱,关押他的笼子才会自动消失,烧红的火钳也才会消失。
否则,他将被永远关在那只笼子里。
笼子。
哪里没有笼子啊?
两天后,毫无指望的焦光忠突然想到了老袁,麻木老袁。
怎么没有早一点想到他呢?还是原本不想动他?捡垃圾的老袁,麻木袁克隆不就是天遣的灵感吗?不期而至的旨意。
就像一道胜利的闪电划破夜空。
他是前来拯救焦光忠的人。
是他的贵人,是施与他恩典之人。
帆布棚子,以及埋没在垃圾堆里的床铺。
天哪,焦光忠确信那里收藏着老袁一生的积蓄。
起码也是部分积蓄,卖垃圾的钱都在那里。
他的鼻子嗅到过钱的味道,也嗅出了钱的位置。
天哪天哪,老袁对不起啊!
焦光忠直奔帆布棚子而去。
老袁又到外面捡垃圾去了,棚子里空无一人。
没有哪个地方上锁,到处都敞开着。
老袁毫无戒备之心。
没有人去偷窃一个捡垃圾的人,也没有人相信捡垃圾的人值得一偷。
老袁把自己活成了一块垃圾,没有戒心是正常的。
他不欠这个世界什么,他是被扔掉的,谁会把他捡起来?焦光忠鼻子发酸,想抽自己的脸,狠狠地抽自己的脸。
他厌弃自己,另一方面又感激老袁。
危难时刻,冥冥之中还是老袁在帮他。
他掀开床铺,里面的景象让他惊呆了。
他的嗅觉是对的,他能准确嗅出金钱的味道和位置。
这是他的天赋,他的嗅觉没有欺骗他。
破烂的袜子、袖管、手套、内裤、破布条、烂手帕。
总之,所有那些能够缠裹钞票的东西,那些能够盛装的器物,里面都零零碎碎地塞着些钞票。
有零票子,也有整票子,还有钢镚儿。
它们混在垃圾中,也像垃圾,无法清理。
焦光忠将拿到手的钱拢在一起,拢成一小堆。
他只取了老袁积蓄的一部分。
据目测,大约有他所能看到的三分之一或一半。
他坐在那里,慢慢清点细数。
很难数,各种额度的钞票和零角子。
这一小堆金钱,共计一千三百二十多块。
焦光忠只拿了一千块,剩下的钱他又铺在床铺下面。
一千块钱就这样到手了。
我偷了老袁,我他妈偷了老袁,但是我一定会还给他。
老开信守承诺,收到赎金,就把笔记本退给了焦光忠。
焦光忠怀抱笔记本上楼,就像怀抱着昂贵的战利品。
焦美丽把它说成是饭碗,全家人的饭碗,他不能砸了它。
这会儿他想到要给钱素素打个电话,让她安心。
接电话的人却不是钱素素本人,而是另一个人。
她很平静地告诉焦光忠,钱素素昨夜去世了。
焦光忠站在楼梯上有些恍惚,这不是他愿意听到的消息。
他的本意只是想告诉钱素素,这件事情他已经处理妥当。
他丝毫没有责备她的意思,相反他要请她不必在意,更无须愧疚。
钱素素已经听不到他说什么。
她的结局证明之前她所说的话并非危言耸听。
焦光忠手搭凉棚看着下边,看着远处。
他记得回来那天,也是站在这里,也是手在额上搭着凉棚远望。
正是在这里,他看到了老袁。
当时,老袁在干涸的水塘底部捆扎垃圾,也是这样手搭凉棚望着他。
他们望着彼此并认出了对方。
焦光忠拿下额上的手,继续往楼上走。
可能是抱着笔记本,也可能是平衡出了问题,他从二楼那个地方摔了下来。
楼层并不高,焦光忠伤得不太厉害。
没有伤及生命,只是他另一条腿可能也会瘸掉。
幸运的是笔记本被他牢牢抱在胸前,并且不是那里先落地,所以笔记本也没有损坏。
焦美丽是最先赶来的人之一,她首先查看了哥哥的伤情。
还好,他还能说话,意识也算清醒。
焦光忠说:“笔记本我赎回来了,不是我偷的,也不是我卖的,但我还是赎回来了。
”
焦美丽先接过笔记本,再伸手扶起他。
“赎笔记本的钱也不是我偷来的,是我借来的。
因为我给麻木写了张一千块钱的欠条,欠条就压在他床铺里面。
我是认真的,有借有还。
他不一定能看到,但欠条我肯定写了,也给他了。
”
“麻木是谁?”
“老袁,袁克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