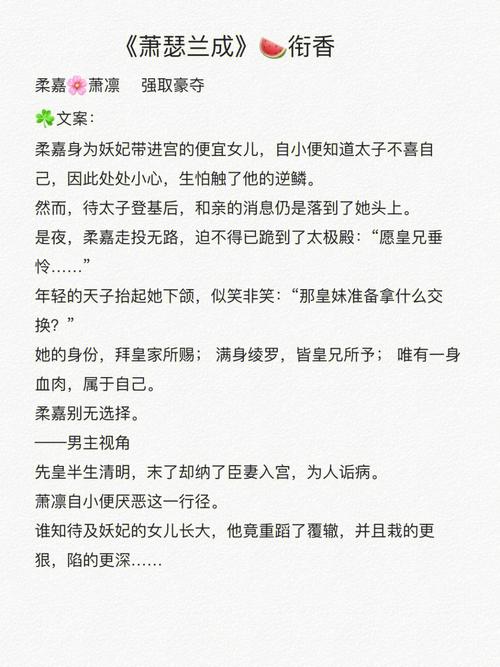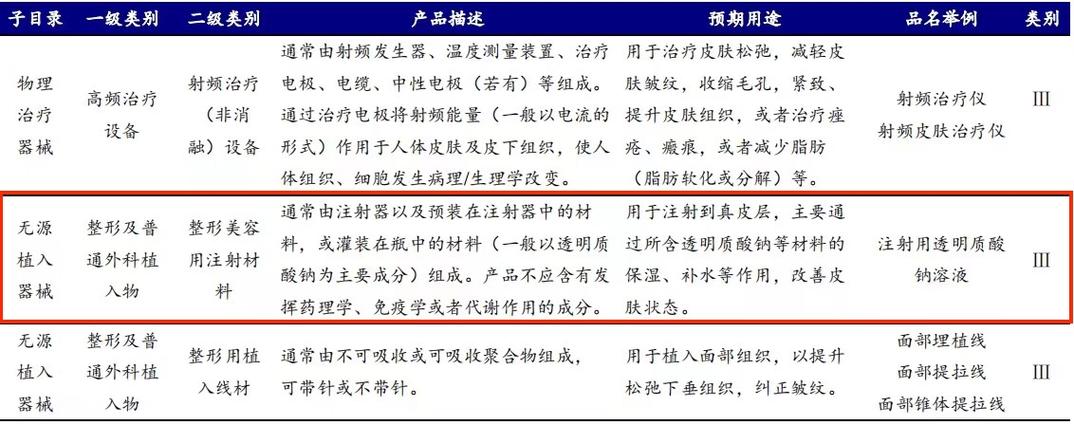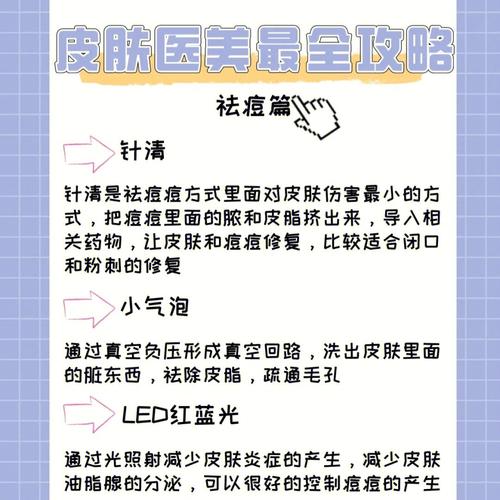“率性而动_禀之造化”——论《野马_尘埃》之先锋性(野馬塵埃先鋒)
在回顾《野马,尘埃》的创作时,作家提到:“我始终将文学创作扎根于民族文化,忍受孤独,锲而不舍。华夏民族在世界文明发展历史中创造了丰厚丰富的灿烂文化,我的敦煌文化系列探索小说,包括《野马,尘埃》,仅仅是一个文学探索者的抛砖引玉之作。”[1]作为一部兼具人文情怀与文化积淀以对抗碎片化书写的长篇小说,《野马,尘埃》扎根于纵深的中国历史,选取唐朝作为故事背景,以禅宗传播为线索进行共时性的铺陈展开,即以吐蕃、回鹘、粟特、匈奴、楼兰、大夏、大月氏等西域各民族部落史,以及古希腊、罗马、古巴比伦、印度等西域诸国别史为参照物,造就出一部有关丝路历史文化的大书。《野马,尘埃》打破传统历史小说的结构与叙事,将皇帝、大臣、商贾、僧人、平民等众生相归置在虚幻与非虚幻的符号化场域中,使之成为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作家在探索历史文化之丰厚的同时,不忘关照现实之诡谲,因此在作品中表现出鲜明的先锋性特征。
冯玉雷与文友胡秉俊(中) 、朱建军(左)在文学艺术活动中合影
《野马,尘埃》在文体选择、语言叙述等方面颠覆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创作模式,加之符号化的现代性书写,叙事层面的断裂和虚幻处理使小说文本的生成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正如作家在后记中所述:“为了消解海量信息冲击时带来的纷繁感和压迫感,我尽量通过语词让人物身份清晰,彰显个性……为了强化表达效果,我还有意让叙述者随着思想感情剧烈变化混用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方言甚至流行语中的第一人称代词。”[2]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混用几乎贯穿小说叙述的始终,主要表现在小说人物的对话之中,如张九龄与李泌对话:“此怪物不除,他日必生事端,将贻害无穷。吾愧为张良之后,但恨无先祖大才,只能坐视妖怪横行,岂不悲哉!
”[3]使用雅致的文言文的同时,还有浅俗的白话,如唐玄宗在给安禄山的信中写道:“可爱的小白痴‘三百斤’,朕本来要通过这个游戏提高你的文化品位,没想到推广这么难!
还是用爱卿提供的、通俗易懂、利于快速传播的‘干瞪眼’吧!
”[4]二者交替出现,丰富文本内涵的同时,增强了感情的渲染。除人物对话外,小说的叙述语言中也大量存在着此类例子,“但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朝圣者,怀着为人畜祈福、超度亲人亡灵、打仗获胜、禳灾、求贵子、求超级肉苁蓉、求美容、求暴富……”[5]小说中还有许多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词语,诸如“房奴”“宅男”“贫九代”“官四代”等。地域方言的使用也别有兴味,龙长盈、贺保定、张延住等人用兰州方言展开激烈的对话,“夯怂”“背扇”等方言俚语的使用,不仅强化了情感的抒发,而且消解了历史高高在上的隔膜与神性,拉近小说与当代读者的距离,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和互文性,体现出先锋性创作求新求变的宗旨。除此之外,小说表现出多种文体交互使用的特点,化用《庄子》寓言及古代神话传说入小说,并以“混沌”“倏”“忽”作为小说虚构主体的重要部分;还有《黄土部 会盟》的叙录,《黄土卷 赤松德赞关于顿渐之争的第壹道敕令》的敕令,《红火卷 阿嗜尼第壹道奏表》的奏表,《玄武版卷 印象?女祭司》中的批注、文书等。多种文体穿插使用,加强了小说的表达效果,与小说中博杂的人物画卷相符合,以满足不同叙述者的身份需要,同时丰富了文本的内在张力。小说采用符号化书写的方式,将作家自身的审美体验,即由作家创造的一种艺术信息借语言符号表现出来。[6]主要体现为对阿嗜尼的符号化阐释,鼻子上的大痣是阿嗜尼自然形象的符号表征,阿嗜尼本人又是象征着权力继承与更替的傀儡符号,仿佛无生命之物一般没有幸福感、荣誉感,只到顿悟禅宗之道,才于虚空中感受到自己如烟波一般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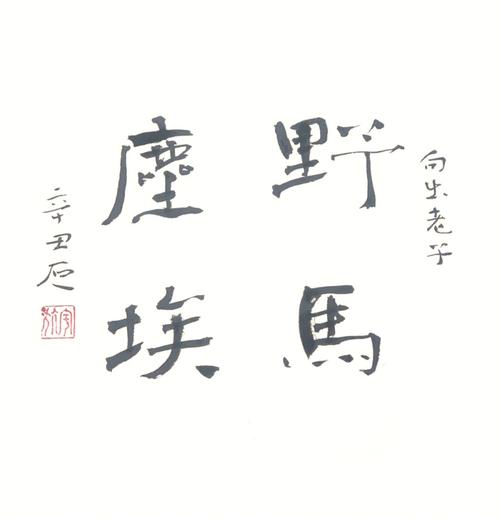
刘晋汝
作品中字里行间流露出宏阔的历史积淀,文风爽利磅礴,作家以写史之客观现实精神进行小说创作,同时又表现出神话般的魔幻诡谲风格。小说中存在大量与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不相符的意象和语词,使文本超越了时空限制,渲染出浓郁出彩的诡谲之风。《玄武版卷 印象?女祭司》叙述了鄯善大祭司、后凉大祭司、后秦大祭司、西凉大祭司等,叙述语言及事件多采用时下流行的网络用语或与女性相关的轶事。“别在我的坟前哭,脏了我的轮回路”“男人是条万能狗,谁有本事谁牵走”,尤其是“鸵鸟的幸福,只是一堆沙子”[7]的反复出现直至本节终笔,尽显无厘头的戏仿之味。女性为宣传保护动物做裸体模特、玛丽莲梦露等八卦闲聊被纳入女祭司众生相的刻画中,与“安禄山”“突厥”“”等符号意象交融出现在同一场域,建构出一场现代性的历史狂欢。以卑猥渺小消解崇高伟大的反讽也成为《野马,尘埃》虚魔幻色彩的重要手段,小说将“野马”定义为马之实物与撄人心之精神力量两类,不论虚幻还是真实,“野马”的影响力都是极大的,“野马行动处,常常伴以遮天蔽日之尘埃,久久不散。”[8]如祁连山一般高大绵长,令戈壁荒原臣服的野马,却产生于“疏勒河岸边一个牛虻的喷嚏”,宏大庄严与卑微渺小的同一与对立进一步深化,“空中掉下的野鸭屎打断了它的腰。如果不是芦苇的汗气及时弥补它的伤口,野马将不复存在。”[9]以腌臜之物作为反讽的中心,在伟大与渺小的轮回之中,展现出万物本源的同一性,崇高正在这同一性中被消解。《味版卷 忍者的表演行为》“马其顿狮子”亚历山大死于疟疾,这一仓促平庸的死法与正在进行的英雄崇拜形成对立,正是“命运之神对英雄最大的嘲弄。”[10]作家利用反讽的手段,用卑猥之物解构宏大意象与形而上学的理性,背离中心主义与秩序化的同时,体现出以“否定”为主导的先锋精神,从而构成艺术话语与时代精神的双重悖论。
冯玉雷与评论家赵录旺等合著《敦煌文化的现代书写》封面
通过打破时空限制,在现代与历史的互文中,作家借内在律的诗美观念,将人心的自由境界与反叛精神相互交融,以丝路文化为载体,使小说体现出别具一格的先锋精神。“我心中除了野马,一无所有”“野马没有与生俱来的辔头”,[11]野马作为自由与野性的抽象符号,既是小说的中心意象,又是作家文学理想与精神力量的寄托形式,将火光般燃烧的生命力量和精神信念借助巨大的意象表现出来。以驼轿为历史参与者和叙述者创作的文本内容是作家内在律诗学的集中体现,“驼轿记忆之冰被那一声呐喊击破,道道裂纹呈辐射状向四周迅速扩散。每道裂纹都通向那些被淹没的历史”“现在,沉睡记忆被唤醒,原始证据不断增加,驼轿条分缕析,要整理一部完整的历史”,[12]驼轿被赋予生命和思想,成为历史更替的见证人和讲述者。驼轿戏耍杨国忠、玄宗过分依赖驼轿等非现实情节的穿插,展现出战乱年代的怪诞和人心的恍惚,在这充满黑色幽默的反讽中,历史也被驼轿载着颠簸前行。符号学家赵毅衡称反讽并非犬儒,而是最认真,“承认彼此各有是非,却不借相对主义逃遁。欲在当代取得成熟的个人性与社会性存在,反讽是唯一的方式。”[13]因此在反讽和否定的奇特场域中,作家将文化视作无所谓进步,而是“始终有一种回跃,不断回到人类生存痛苦的老问题上去”,[14]借摩诃衍之口表现出有关禅宗四大皆空思想的反思。一切非本我之物都如转瞬即逝的白云一般留不住,物质和肉体只是大梦一场空,真正的自我应是精神的自由与心灵的佛性。
这正是《野马,尘埃》一书所表达的重要精神内涵,作家以坦率狂热的感情、虚构与非虚幻交互的反讽手法,在极具先锋性的荒诞意味中,凝聚了他对时代注入的生命激情与自由信仰,传达出文化传承与精神重建所需要的力之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意义与现实价值。
注释:
[1][2][3][4][5][7][8][9][10][11][12]冯玉雷:《野马,尘埃》[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980,987,68,92,112,558,181,523,509,106,253页。
[6]安和居:《“符号学”与文艺创作》[J],《文艺评论》,1985-01(01)。
[13]赵毅衡:《反讽时代:形式论与文化批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0页。
[14][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6——60页。
作者简介:
刘晋汝,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