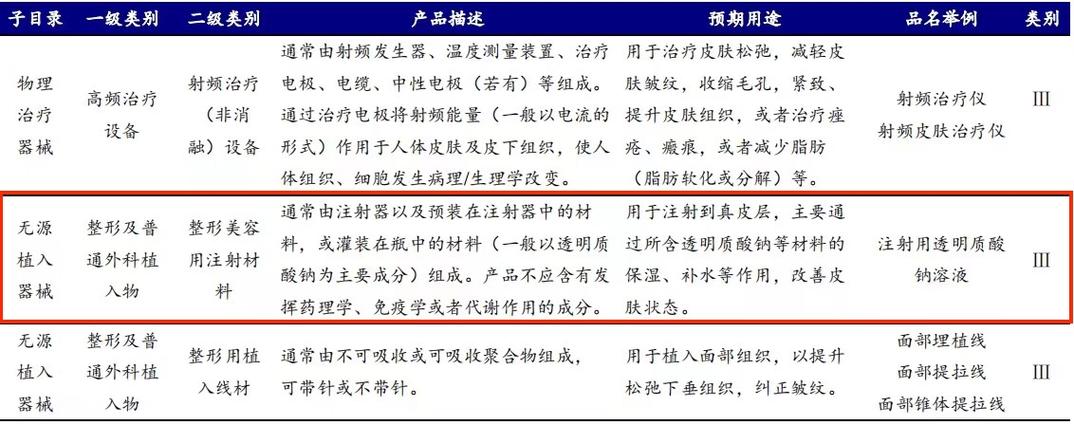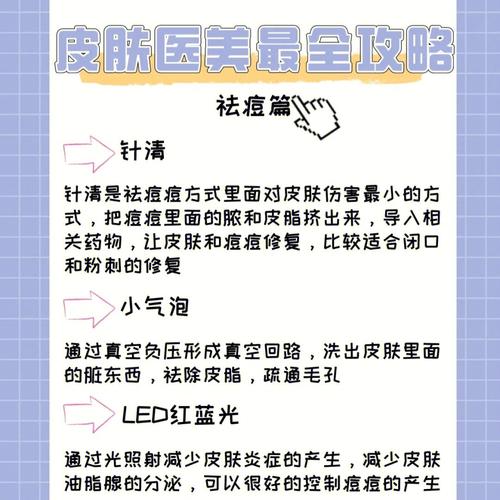家暴之后:一个县城女人的伤痛与选择(縣城選擇丈夫)
25岁的杨宁在等待一场与前夫有关的宣判。
470天前,她以近乎决绝的方式结束了正在进行中的家庭暴力:在前夫轮番落下的耳光和拳头之中,她选择从二楼的窗户跳下逃生。
在不过百万人口的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即便顶着熟人关系的社会压力,杨宁也不愿成为家暴中沉默的妻子。她形容过去那些家暴中的受害者,“就像是被拐卖进大山的女孩,逃都逃不出来。”

于是,原本性格内向的杨宁主动撕开婚姻的伤口,将监控拍下的家暴视频公之于众,并坚持离婚,将前夫对自己的人身伤害诉诸法律,并试着从对他的怨恨中逐渐抽离出来。“只要拿到判决书,我心里就会把这件事放下,就当是生了一场病。”
和其他家暴受害者相比,杨宁说自己是少数“被外界看到的人”,更多的女性不敢发声、不能发声以及发声后没被看到。
杨宁从二楼窗户跳下后的画面。视频截图
“如果有更多的人提前看到就更好了”
一年零三个月以来,杨宁几乎没有睡过整觉。
那场家暴之后,救护车把她送到医院时,她全身骨折7处。除了前夫一拳击中的左侧眼眶内侧壁骨折,更严重的伤害是由高处跌落造成。她的胸椎、腰椎、双跟骨、耻骨、骶尾椎骨、髋骨呈现不同程度的粉碎性、压缩性和爆裂性骨折。医生当时给出的诊断意见是截瘫。
三块钢板和数枚螺钉植入她的身体中,在左右脚踝各自留下一处L形疤痕。后背到腰部的手术痕迹更明显,是一条沿着脊柱竖直、约为20厘米的刀口,每隔一段就有一条短横的缝合痕迹,就像是冬天女孩们常穿的牛角扣大衣全部系上的样子。
杨宁背后的手术刀口痕迹依旧清晰。受访者提供
她时常在半夜醒来,被那种混杂着电击、灼烧和针扎的感觉折磨着,有时持续十来分钟,有时长达几小时。她形容这种绵长的痛苦,“不是发生在某个瞬间,是日复一日、每时每刻,夜晚最明显。”
除了药物,唯一有效的对抗方式是转移注意力。大脑已经困到极致,眼睛也睁不开,她只能把手机放到枕头边,光听视频里的声音。黑暗中,耳朵的听觉被放大,疼痛感便能缓解,再抓住下一次睡意袭来的间隙入眠。
杨宁皮肤白皙,双眼皮,喜欢把染过的长发扎成一束马尾。像这个年纪爱漂亮的姑娘一样,她会涂上豆沙粉的指甲油,自拍时配上花朵特效的可爱滤镜。
2017年大学毕业后她从郑州回到柘城,靠着自己经营的一家女装店,过着没有太多经济压力的日子。“那件事”之后,她把原本的店铺转了出去,和朋友栗子一起把新店搬到房租更低的一条巷子里。
一天之中的大多数时间,她都待在这里。小店装修成时下流行的白色风格,地面是原始的水泥色,搭配着仿真绿植,清新简约。当她套着长裤坐在沙发上时,看起来和进到她服装店的女孩们并无二致——只是手边多了一副灰色的拐杖。
杨宁的身体还在康复中,目前靠拄拐。受访者提供
过去,她觉得“家暴”是一个离她很遥远的议题。当她在微博率先曝光了自己的经历,不少网上的陌生人和身边的同学,都来向她倾诉类似的家暴遭遇。
她惊讶于亲密关系中有如此多的女性曾经或正在经历家暴,更加关注那些被家暴的女性——比如宇芽和拉姆。
当她在一个知识分享平台搜索到关于“家暴者的共同特征”时,心里一怔,“如果自己早点看到多好”,转而又想,“如果有更多的人提前看到就更好了。”
房门内的暴力
前夫王立凯皮肤白净,个头超过1米8。留给朋友们的印象大多是“客客气气”、“笑起来蛮阳光”、“挺老实,还有点有趣”以及“家里条件挺不错”。看上去与凶狠无关。
以至于杨宁某次说起她可能会被丈夫“收拾”的时候,朋友栗子并不太相信,“他真的会动手吗?会打你?”
但关起房门,在外人看不见的地方,暴力不止一次降临在这段并不算长的婚姻关系里。
杨宁说,第一次动手发生在孩子四个多月时。晚上喝酒回家的王立凯与她发生激烈争吵。当着公婆的面,杨宁第一次被打头、摔在地上、扯头发。王立凯毕业于体育相关的专业,人高力气大,家人试图拦,但是拦不住。
她说,第二次动手是2019年7月的一个下午,她再次被扇耳光、手臂捶至淤青,这一次王立凯没有喝酒。
这对年轻的夫妻相差一岁,毕业于同一所高中,大学时又都在郑州。与杨宁认识超过8年的朋友张希悦,她看着王立凯从高中时候开始追杨宁,一直到大学时在一起,“王立凯是她的初恋,唯一的男朋友。”
2017年5月3日,两人举办婚礼。同年10月,杨宁和王立凯的儿子出生,并于2018年12月办理结婚登记。
婚后的王立凯一直没有工作,两口子之间的开销大多由杨宁支付。时间久了,杨宁对于丈夫不出去工作的状态感到厌烦,“我有经济收入,共同生活付钱我不计较,但他老向我要零用钱我不是很喜欢,这个不应该我承担。”
王立凯去网吧会找她要钱,点外卖也会用她的手机下单支付。再后来,丈夫回家越来越晚,杨宁并不清楚他的具体行踪,只知道他大把时间花在打麻将、玩纸牌上。
杨宁和朋友新开了一家店,搬到房子更低的巷子里。新京报 杜雯雯摄
王立凯对妻子的询问也变得越来越不耐烦,好几次争吵都是因为婆婆试图管束去牌场的儿子,被王立凯当做是妻子“打小报告”。但他对于杨宁的外出却多有控制,杨宁去跟朋友吃饭,他会问清楚是跟谁,有没有男性。杨宁去美容院做护理,他会拨视频电话过来,确认环境和人员。
直到2018年,追债的人拿着欠条找上门,杨宁才知道王立凯在外赌博欠下了几十万的债。杨宁说,王立凯名下没有房、车和现金,他欠下的赌债最终由其父母出面偿还。这些借款,有的是王立凯以生意周转的名义借出。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能查询到王立凯与多人存在民间借贷纠纷的民事判决书,涉及金额从2万到10万元不等。一份民事判决书显示:王立凯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理由是他向沈某借的十万元属于非正常借贷关系,款项用于赌博,沈某明知王立凯借款是用于赌博,该笔借款不应受法律保护。最终,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认定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对于沈某要求偿还借款的请求予以支持。
11月中旬,与王立凯母亲庞敏有过两次交谈。她否认儿子赌博、指责杨宁自编瞎话,以及担心事情闹大对孙子的成长不利。提到杨宁遭家暴,她说,“被打是有原因的。都是女人,这句话不明显吗?”她还说,“(儿子)要是有罪,就治罪。”
对于杨宁来说,这并不是她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答复。她认为,那些不善意、“泼脏水”的话,是王立凯家人在给他找理由。“找一个打我的正当的理由,小县城里,他们觉得这样的话会让外人理解,会让别人对他们恶意不那么大。”
早在杨宁第一次被打后,家人就支持她离开身边的男人。但事后王立凯来向她悔过,杨宁觉得孩子还小,丈夫此前也并未有类似举动,从内心而言她也不想完全放弃这段婚姻,甚至找理由安慰自己,“是不是酒精的原因?”
直到第二次暴力也毫无缘由地到来,杨宁才坚定了离婚的念头,她和朋友栗子提到想找律师咨询,还考虑把店铺转出去。但她还没来得及付诸行动,便等来第三次更严重的家暴。
选择逃生
柘城县最繁华的中心正对着容湖景区。这里有宽阔的广场和几条延伸的商业街。一年前,杨宁的店就开在广场上的女人街。单从环境来判断,这里原本是最热闹也最安全的地段——她的店铺西侧100米,便是城关派出所容湖警务室。
但事后回想起来,杨宁觉得2019年8月13日丈夫对她的施暴,早有预兆且无法逃开。
事发六天前,她与丈夫王立凯在电话里有过一次争吵。那天下午,杨宁的婆婆希望从儿媳这里得知儿子的去处,当她在一个牌局上找到儿子后,当着打牌的人面骂了王立凯。王立凯觉得是妻子向母亲告状“泄露了他的行踪”,他在当即回拨给杨宁的电话中大发雷霆,并表示“要收拾她”。
威胁的电话打来时,大约是下午四五点,天还没黑,杨宁接完电话心中不安,便和自己的母亲一起回了娘家。夜里,她先后收到婆婆发给她的两条微信,一条是带着提醒意味的“关门快走”,另一条的大意是“委屈你了,让他好好反省”。
之后几天,杨宁和王立凯没有任何联系,只听说他去了郑州。8月13日,杨宁在家中吃过午饭后到了店里。没过多久,王立凯推门进来。
杨宁记得,见面后两人在言语上没有发生剧烈冲突,都是一些琐碎的、找不到重点的对话,比如为什么最近没有联系。她对于危险的到来毫无察觉。
服装店内外各自安装了一个监控,这个原本为了防盗的摄像头,意外记录下短短20分钟内,王立凯施暴的全过程以及杨宁坠楼的一瞬。
13时19分,王立凯突然抓住站在一旁的杨宁双肩,猛地往地上一推,杨宁没有防备,失去重心,朝后重重倒下。一分钟之后,王立凯高抬的右手朝仍躺着的妻子一记耳光。他下手不轻,以至于打完人后顺着这股力朝前走到了收款台。
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双手扯着杨宁的长发在瓷砖上拖行,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耳光、拳头。
比起妻子的被动和畏惧,王立凯有时会两手叉腰歪站着观察对方被打的反应,有时半蹲着近距离朝低头的女人训话。13时24分,王立凯走到门口,把玻璃橱窗两侧的窗帘通通拉上。一把黑色的钥匙在他手上甩动。
王立凯收走了杨宁的手机,导致她无法向外求助。13时20分,杨宁找到一个机会,快速跑到门口想逃出去,当手刚刚拉开一侧的玻璃门时,王立凯瞬间抓到了她。她用力拽着把手不放,却被丈夫锁住脖子,扭翻到地面,还撞到了店里一辆粉色的小推车。
杨宁试图拉开店门逃走,被丈夫拉回摔在地上。视频截图
13时33分,一楼监控捕捉到最后的画面:杨宁为了躲开拉扯蹲在沙发前,被王立凯从背后架住抬起。男人一边打开通向二楼的白色小门,一边将妻子拖了上去。五分钟后,穿着黄色短裙的杨宁从二楼窗户跳下,光脚落地。
杨宁坠落时,栗子正站在服装店的一楼门外朝里张望,听到身后的响动,她也吓得抖了一下。栗子的老公随后拨打了120。
在那之前,栗子听到了旁边传出的哭打声,她特意过来敲门询问里面的情况,并让王立凯打开门。王立凯隔着玻璃告诉她,“我们在吵架,一会儿就开门。”说话时,王立凯挡住了屋内大部分的视线,脸上也没有异样的表情。那一刻,杨宁坐在沙发上擦鼻血,站在外面的栗子只看到了白色纸巾,以为小姐妹在擦眼泪。
杨宁说她真正感到害怕的时刻,始于丈夫对她左眼的重重一拳,“当时整个左眼都看不见了,觉得眼睛瞎了,脑子里也一直嗡嗡响,我才开始崩溃。”
许多人后来问过杨宁,为何一定要选择跳楼这个方式。她一遍遍解释,在那个被收走唯一的通讯工具、无法逃出求助的场景下,面对拖上二楼后的未知,跳楼不是为了寻死,而是求生。
“关于跳楼,我其实是后悔的,特别是腿部疼痛的时候。但这是基于当下我脱离了危险的处境来回看,如果把我再放进当时的场景,我还是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穿行过地狱之后,光明才缓缓降临
跳楼逃生一年后,杨宁才算真正意义上与这段给自己带来伤害的婚姻解除了法律意义上的关系。
初夏之前的六月,她的身体恢复到可以坐上轮椅,便在家人陪伴下前往当地法院递交了申请离婚的民事起诉书,她的要求只有一个:孩子的抚养权。
但7月14日的那次开庭,王立凯不同意离婚,并表示家暴是意外,夫妻感情并未破裂。一个月后,一审法院依法判决准予离婚。王立凯再次上诉后的9月18日,商丘市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宁坚持离婚,并拒绝出具谅解书。已成为前夫的王立凯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羁押,将面临刑法的裁决。她也切断了和王家的所有联系,电话、微信都没有往来。其实县城并不算大,即便是换了新地址,从她的新店走到王立凯的家也只需10分钟。
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杨宁的部分身体。手术后,她先是经历了长达三个月的卧床休息,然后靠自己手撑着能缓缓坐起来,再过渡到坐上轮椅踏出病房之外的空间。现在,她可以拄着单拐一深一浅地行走。
在这之前的一年里,她像初生婴儿一样,重新开始学习翻身、静坐、站立和行走。三月的时候,她在一条视频里配文写道,“在医院度过了夏天、秋天、冬天,某天看窗外发现绿树,春天来了啊。”
但仍有一些不可逆的损伤无法修复,比如脊髓和神经。左腿肌肉萎缩明显,左脚也出现足下垂的症状,需靠足托固定,而她的右脚则随时处在肌张力的状态,紧绷上翻。
每天早上八点,大哥杨志华会骑上一辆套着透明防风罩的电动三轮车,送她来离家十来分钟车程的柘城县中医院康复科。四个小时的康复治疗,要经过蜡疗、针灸、手法三个阶段。她的医生说,持续的康复治疗可以防止她的肌肉挛缩、僵直和粘连,未来或许可以“脱拐”,但恐怕无法恢复到正常人走路的步态。
杨宁在医院做康复治疗,医生说未来她或许能脱拐,但步态难以恢复到和正常人一样。受访者提供
起初,除了最亲近的家人和现场的见证者,没有太多人知道她是因何受伤。有朋友听说她住院了来探望,她觉得委屈又不想多说,只是眼泪吧嗒吧嗒地掉。
她害怕别人看她的脚,也担心对方来问原因。就连服装店的店员和一些熟客问起,她也只是回答,“是意外,不小心摔倒了”。
在哭泣和沮丧中度过了一段时间后,她还出现了特定场景下的心理创伤。从医院回到家中时,一对男女在家门外嘶吼,她紧张得蒙上被子,又总是忍不住去听他们争吵的对话,条件反射似的害怕和出汗。
后来,她尝试把自己从情绪的黑洞中拉出来。她开始在网上搜索脊髓损伤和下肢截瘫的医学知识,想从别人的案例里找到借鉴,而后又查询与残障人士相关的生活状态和服务保障,总觉得“提前了解这些会对自己有帮助。”
但最让她介怀的是,事发至今对方都没有向她表达过歉意。她无意中听朋友说,对方在一些场合表达过“在县城里有关系”的言语。她气不过,又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干脆甩开面子和亲情捆绑的包袱,在朋友圈和微博公布了自己被家暴的视频和文字说明。
很快,视频的内容迅速登上热搜,杨宁被家暴的事在县城内外都引发关注。法院打电话给她母亲,表示会依法公正审理此案,市里和县里的妇联工作人员也每隔一段时间询问她的境况。
自揭伤疤的曝光,让杨宁在舆论上得到同情和支持,却让她和对方家族的关系更加恶化。有朋友担心她被报复,她也会焦虑,但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过想法,“我不会因为他可能会再次伤害我,就放弃对他的刑事责任追究,这点我没有变,从一开始就非常坚定。”
因此,当她在网上看到李阳的前妻Kim原谅了对自己施暴的丈夫,她感到困惑,“完全不懂,我不知道她这种做法能不能改变一个男人,起码现在来看,我不理解。”
但对于那些正处于家暴,因为各种原因无法马上离开、还在默默忍受的妻子或女友们,她却有更多的同理心。“毕竟他第一次打我的时候,我也是选择了原谅。我们只能用事后的眼光去评判当时的选择是错误的。”
她能理解那种不知所措的迷茫,“我没有资格去否定,说这种是一种什么愚蠢的想法。跟我第一次遭受家暴一样,毕竟以后的事谁也不知道,当时只是抱着一种‘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不会再重复’的想法。”
她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在一条仅自己可见的微博中,她这样写道:接近死亡反而更无惧死亡,既然活下来了,就该让伤害我的人得到起码公平的惩罚。
七月份的夏日,她收到一束朋友送来的鲜花,白色、粉色和浅紫色玫瑰搭配着康乃馨、小雏菊、洋桔梗和尤加利叶。淡粉色的包装纸围绕着星星纱网,一片温柔。卡片上只有短短的两句话:穿行过地狱之后,光明才缓缓降临。
(文中杨宁、王立凯、杨志华、栗子、张希悦、庞敏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