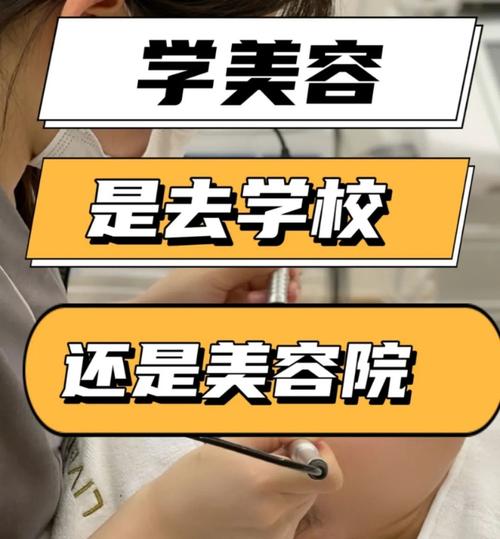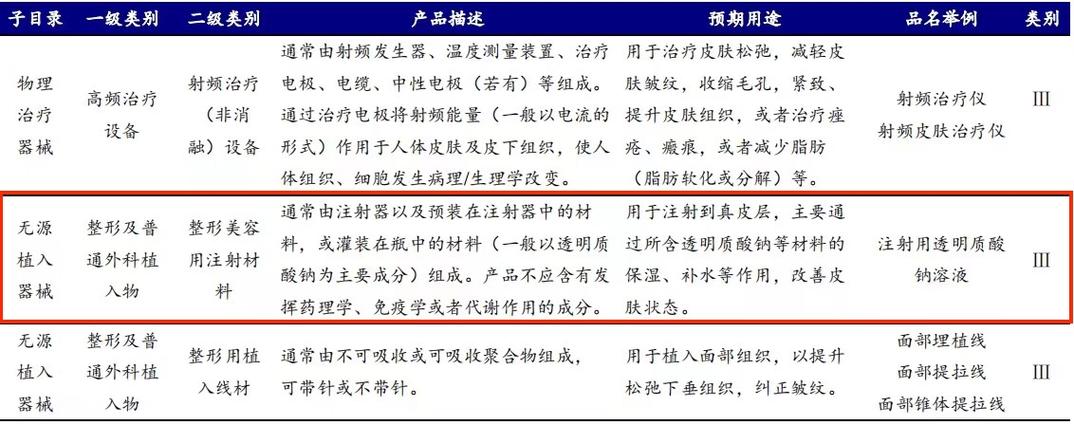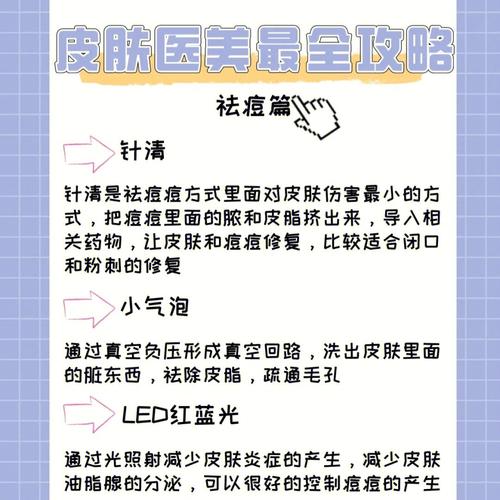苏轼词中的女性形象新变(蘇軾形象女性)
词至晚唐五代,渐趋柔靡,词作中的女性形象越来越符号化、类型化,对女性情感的描画大体不脱离情与艳情的窠臼,充满了寄情声色的脂粉气。进入北宋以后,欧阳修、晏殊等文人以余力作小词,稍有改观,“风流蕴藉,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词至柳永而一大变,他不但创制新声,拓展词境,而且大力发扬民间词的传统,语言通俗,自成一体。柳永擅长描写青楼妓女和漂泊失意的文人等下层人物的生活和心理,对歌妓思妇的爱恨悲欢描写大胆泼辣,但常常带有男性视角下的狎玩之意,所以李清照在《论词》中批评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
这一情形的改变,有待于苏轼大踏步地进入词坛。金人元好问说:“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新轩乐府序》)在苏轼的词中,女性形象与前人作品相比,有诸多新变,别具情韵。
真纯自然的形象之美

从描写对象来看,苏轼词中的女性形象更为丰富,除了歌儿舞女,还有妻子、侍妾、村姑。这些女性形象大多真纯自然,散发着生命的光彩。这种描摹和欣赏是非功利性的,以虚静之心烛照女性之美,透过形象而传其神韵,呈现了人性之美的鲜活;不再是特定群体的类型化、抽象化,而是跃动着生命力量的独一无二的个体。
苏轼被贬黄州时,与知州徐君猷往来过从甚密,徐家后房佳丽甚众。元丰五年(1082)十二月,监鄂州酒税张商英过黄州,会于徐君猷家,苏轼应邀写下《减字木兰花》五首和《菩萨蛮》一首赠予侍女和笙妓,虽未完全摆脱“词为艳科”的樊篱,但格调清新,艳而不淫,描形画貌,言简意深。比如其中的两首《减字木兰花》:
娇多媚杀,体柳轻盈千万态。殢主尤宾,敛黛含颦喜又瞋。徐君乐饮,笑谑从伊情意恁。脸嫩肤红,花倚朱阑裹住风。(妩卿)
天真雅丽,容态温柔心性慧。响亮歌喉,遏住行云翠不收。妙词佳曲,啭出新声能断续。重客多情,满劝金卮玉手擎。(庆姬)
写妩卿,一“笑”一“从”一“恁”,传达出动人的意态,一“倚”一“裹”,展现出柔美的风姿,全方位地活画出一个玲珑剔透的侍女形象。写庆姬,从容态之美到心性之慧,从妙词佳曲到情意之真,突出其善良的心地和高尚的人格,没有半点狎邪气息。对于描画人物,苏轼强调“得其意思所在”(《传神记》),就是抓住人物最见个性、最显本质的特征,由形入神,从而展现出人物独有的风姿与神采。苏轼写侍女,正是抓住了其各自的传神之处,略加点染而呼之欲出,形象真纯自然,无一点鄙俗气。
苏轼词刻画女性形象,善于运用衬托手法,以物写人。比如《水龙吟·赠赵晦之吹笛侍儿》:“楚山修竹如云,异材秀出千林表。龙须半翦,凤膺微涨,玉肌匀绕。”叶嘉莹先生在《论苏轼词》中谈到这首词时说,开端几句写笛之材质,便已可见苏轼的健笔高情。不同于一般的俗艳,别具高远的情致。此外,苏轼还特别善于造境,在特定情境中呈现人物之美,比如“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蝶恋花》)“彩索身轻长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困人天气近清明。”(《浣溪沙》)语言含蓄蕴藉,雅丽自然,活画出少女天真烂漫的美好形象。可谓曲尽其形,气韵生动。
除了歌妓侍儿,在苏轼词中,村姑形象也时有闪现,她们真纯质朴,散发着乡野泥土的气息,有如清凉的春风,进一步扫荡了充斥词坛的脂粉气。比如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的五首《浣溪沙》,就塑造了“隔篱娇语络丝娘”村姑形象,“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蒨罗裙”,透过词语,仿佛能看到她们正三五成群相互拥推着、嬉笑着向我们走来。这些更有生命力的女性形象,大大丰富了词作中女性形象之美。
赏心悦目的才艺之妙
苏轼对那些身怀绝技的歌儿舞女格外看重,并常常与之产生心灵的共鸣。这种艺术上的共鸣完全超越了声色层面的需求,而达于物我浑融的非功利的审美体验。体现在词作中,就是对那些歌者、舞者、演奏者妙不可言的才艺之美作了生动的刻画。比如《菩萨蛮》:
绣帘高卷倾城出,灯前潋滟横波溢。皓齿发清歌,春愁入翠蛾。凄音休怨乱,我已无肠断。遗响下清虚,累累一串珠。
上片描绘歌妓之美貌与清音,运用烘托之笔,给人以深刻印象。下片重点写其歌声的动人,通过作者的情感共鸣,写出歌声的哀怨美妙。特别是结句“遗响下清虚,累累一串珠”,想象奇特,言有尽而意无穷。《礼记·乐记》有言:“歌声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累累乎端如贯珠。”白居易《寄明州于驸马使君三绝句》:“何郎小妓歌喉好,严老呼为一串珠。”“一串珠”的比喻专门用来形容歌喉之美妙。
对歌妓艺术造诣更为生动的描写要数《减字木兰花》:
空床响琢,花上春禽冰上雹。醉梦尊前,惊起湖风入座寒。转关镬索,春水流弦霜入拨。月堕更阑,更请宫高奏独弹。
整首词完全集中于演奏技艺的描述,且以取喻见胜。开头一句便以琢玉的音响写琵琶声的清脆,接着以鸟鸣写琵琶声的悠扬婉转,又以冰上雹落写其质实沉闷;下片则以春水流动写乐声的华美,以霜华入拨写乐声的凝重。一连串的比喻写出了乐声的变化与悦耳,与白居易的《琵琶行》同臻于妙。由此也可见,苏轼在欣赏这些歌儿舞女的表演时,不是单纯地视为饮酒助兴的娱乐,更多的是沉浸于艺术的审美享受,并由对表演者技艺高妙的欣赏,进而达于对人生、对世界的体悟。
其他如《浣溪沙》写方响演奏:“远汉碧云轻漠漠,今宵人在鹊桥头。一声敲彻绛河秋。”《南歌子》写小鬟舞蹈:“绀绾双蟠髻,云欹小偃巾。轻盈红脸小腰身。叠鼓忽催花拍、斗精神。”《诉衷情》写琵琶弹奏:“小莲初上琵琶弦。弹破碧云天。分明绣阁幽恨,都向曲中传。”《减字木兰花》写弹筝:“银筝旋品,不用缠头千尺锦。妙思如泉,一洗闲愁十五年。”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表演者技艺的出神入化和艺术境界的高妙,女性的才艺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情深意笃的品性之真
苏轼的一生,大起大落,屡遭磨难,三次贬谪生涯让他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有了更多的体味。他初贬黄州,在《答李端叔书》中说:“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在《送沈逵赴广南》中说:“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可见当时境况之窘迫,心境之孤苦。但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势利,在苏轼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出手援助。而那些歌妓侍儿对这位落难的大文豪大多怀着崇敬之情,对其敬重有加。苏轼在与她们的交往中,不但得到了情感上的慰藉,往往还会激发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感共鸣。故而,苏轼词中的女性形象大多重情重义、感情真挚,表现出情深意笃的品性之美。
“翠蛾羞黛怯人看,掩霜纨,泪偷弹。且尽一尊,收泪唱《阳关》。漫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对人物内心复杂的情感表现得无比真切生动,其感情的热烈缠绵令人动容。“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少年游·润州作代人寄远》)词中没有直接描写思妇的内心波澜,在看似平淡的描写中交代了当时和当下的境况,但在飞花与飞雪的衬托中,思妇内心的期盼、悲苦之情却呼之欲出。再比如“娟娟缺月西南落,相思拨断琵琶索。枕泪梦魂中,觉来眉晕重。”(《菩萨蛮》) “未尽一尊先掩泪,歌声半带清悲。情声两尽莫相违。欲知肠断处,梁上暗尘飞。”(《临江仙·冬夜夜寒冰合井》)这些作品都表现出了女性独有的细腻而真挚的情意。
苏词中对女性情感的描写,并不仅限于两性的爱恋及相思之苦,也有对忠贞、超然、淡泊等情感的赞叹与颂扬,值得一提的是其为好友王巩之妾寓娘所作的《定风波》: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王巩因受“乌台诗案”的牵连被贬岭南,其妾寓娘毅然一路随行。元丰六年(1083)王巩北归,与苏轼重逢,苏轼感慨于寓娘的忠贞和超然淡泊之情而作此词。上片刻画寓娘姿容和才艺,下片以梅喻人,赞颂了她历险若夷的美好情操。结句一问一答,既写出了这位非凡女性的旷达与乐观,同时也寄寓了作者的人生态度。词中塑造了寓娘柔中带刚的秉性、甘苦与共的操守,完全摆脱了思春怀人的模式,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也为苏词中的女性形象增添了亮丽的一笔。
(作者韩伟系辽宁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李菲系沈阳建筑大学副教授)
来源: 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