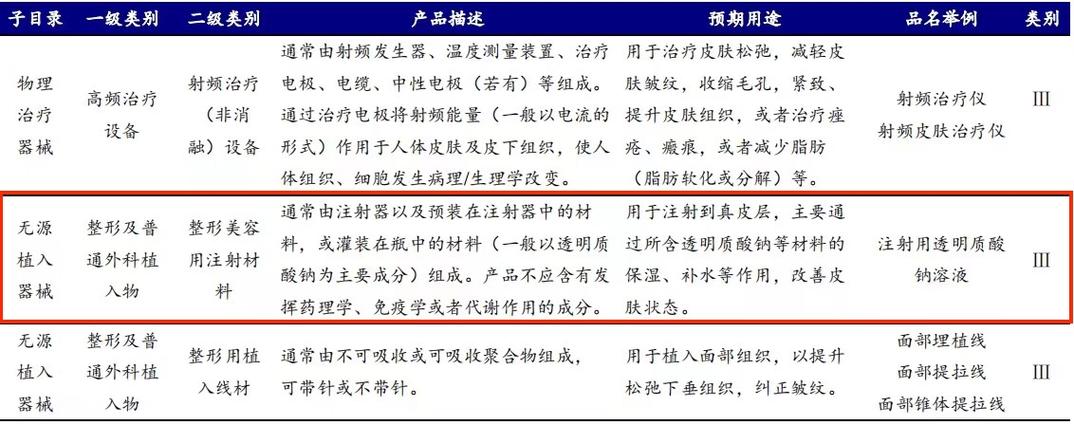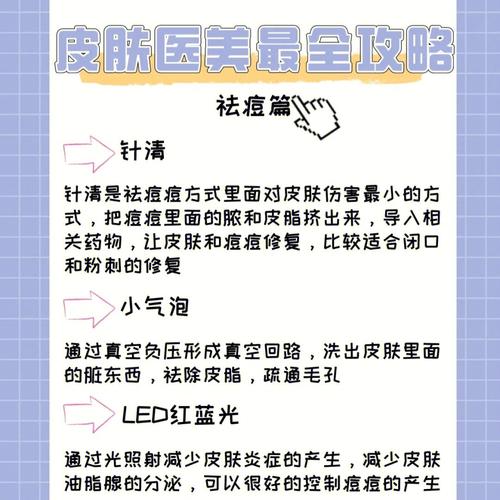在绝美的中国古画里_我们窥见了千百年间的女性生活(女性古畫窺見)
古代典籍,我们可能熟悉《诗经》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对女子美貌的形容,也可能对汉乐府《陌上桑》中“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的美丽穿搭神往。不过,文字描绘始终隔着一层厚厚的迷雾。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持表对菊》轴,图中桌子、仕女的衣袍,甚至书籍函套上华美的纹饰。 ©故宫博物院
所幸,现存的中国古代绘画中,有大量对女子容貌、服饰和日常生活的描绘,这些珍贵的史料里,既有以男性占绝大多数的画家对女子的凝视,也有社会认知,甚至宗教信仰对女性的期待和定义。

「最初的容颜和最早的假发」
有宋以后的中国古代绘画传统,并未如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注重人物,反而在更早的古画中,人物题材更加普遍。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完整女性题材画像,是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战国帛画《龙凤人物图》,画面左上方为一飞凤和壁虎状的龙形,右下方便是一位女性形象。
《人物龙凤帛画》,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湖南省博物馆
据推测,画中人物应为墓主人形象,从中国人“事死如生”的风俗看,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社会流行的女性容装。她身着绣有云纹的长袍,腰间系有大带,还有纤细的腰身,结合“楚王好细腰”的传说,这或许生动地反映出当时楚地对女性身材的推崇;画面对人物的眼睛和眉毛做了细致刻画,眼角和眉梢上扬,近似于“丹凤眼”,说明当时对女性的形体美颇为注重。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素纱单衣,可以看出腰身处做了收腰处理。 ©湖南省博物馆
墓主人头上的发髻特别值得一提,中国女性自古便对头发特别关注,《诗经》中“自伯之东,首如飞蓬”的诗句,说的就是心上人远行后,女性无心打理发型的情节。
发髻也常常在早期绘画中被用作女性的表征。在西汉马王堆一号墓帛画中,墓主人辛追夫人和身后的随行侍女都缠有发髻。有意思的是,考古发现的辛追夫人湿尸头上戴着的,是一顶黑色的假发,在随葬品中还有一顶备用假发,这是中国发现的最早假发实物,当时女性对于美丽容颜的追求可见一斑。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 ©网络
「在德不在貌:古(代男)人心中的女性榜样」
虽然爱美是天性,但中国传统也有刻意压抑女性美的一面,并且对“倾城之貌”带来的危险极力渲染。儒家推崇妇女的四种德行“妇德、妇容、妇言、妇功”,其中唯一和容貌沾边的“妇容”,其实也是在强调仪态而非容貌。
宋代,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女子的妆容淡雅素朴,图为宋苏汉臣《妆靓仕女图》 ©网络
有一类女性绘画题材专门意在道德说教,希望所有女性以此为行为的标杆。这种画像早在汉代画像石中就有反映,如武梁祠画像石中的“秋胡洁妇”,讲的就是秋胡妻洁身自好,斥责秋胡不忠不义的故事。
最有名的“寓教于画”的例子,是东晋顾恺之所作的《列女仁智图》《女史箴图》等。现存的唐摹本《女史箴图》中,有一段画着挂有帷幔的床榻,相对而视的夫妇二人,旁边的题词是“出其言善,千里应之,苟违斯义,同衾以疑”,劝诫女性应该对丈夫说有益的话。
《女史箴图》(局部) ©网络
还有一段描绘两女对镜梳妆,其中一人手持镜子,镜中映出她的容颜,另一位由侍女为其梳头,在她们身边摆放有梳妆盒,从所处的环境和衣着来看,明显都是贵族妇女,一旁的题词说“人咸知修其容,莫知饰其性”,表达的便是古人对女性“在德不在貌”的要求。
《女史箴图》(局部) ©网络
《女史箴图》所呈现的內寝和梳妆场景,都是相对隐秘的空间,这也说明古代女性的活动空间很受限制。在这幅传世之作中,你还可以发现不同场景的女性面容呈现相当程度的雷同,有符号化的倾向,观者往往需要借助旁边的题词才能了解所画的情节,这也说明这类道德说教类绘画对女性的身体和容貌可能存在刻意的忽略。
《女史箴图》局部图,画中女性面容高度雷同 ©网络
「天生丽质难自弃:“发现”女性美」
女性美在画中得不到展示,很大程度上并非出于绘画技法的限制,在战国帛画中,我们已经看到画工非常娴熟地运用线条,即便是《女史箴图》,女子身上的服饰也很飘逸潇洒,颇有“吴带当风”的意味,所以对女子美貌的回避,应该是文化心理的作用;只有到了文化相对开放的时代,女性美才能被“发现”。在唐朝,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强大的国力,都让当时的社会更加宽容、自信,也使得人们敢于正视女性美。
唐《舞乐屏风》图中的女子妆容精致,衣着华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网络
与墓葬帛画中强调女主人死后灵魂的游历、或者道德绘画的说教都不同,唐代绘画中的女性既不是超现实的鬼神,也不是女德的榜样,而是单纯以美色出现。杜甫的诗作《丽人行》中的“丽”,着眼的就是女性的美貌。
唐《弈棋仕女图》中的女子美鬓高耸,簪花耀顶,面色红润,丰盈肥美,衣着华美,突出了女性美。©网络
唐代早期墓葬壁画中,有大量的侍女丽人形象,如懿德太子李重润、永泰公主李仙蕙、章怀太子李贤墓中都有贵妇宫女壁画。其中永泰公主墓出现了规模宏大的侍女仪仗壁画,整个画面就是以众多侍女为主题,各女神态各异,与前朝符号化的面孔发生了很大区别,发髻形式也更多样。
永泰公主墓壁画 ©网络
而章怀太子墓甬道中有一回头仰视的女性形象,别有生趣,她一手仰覆额前,似乎在遮挡阳光,嘴上的胭脂清晰可见,发髻上还斜插发簪,尤其有意思的是因左手举起,衣袖滑落,露出丰腴的手臂。在同时期的画中,女性袒胸的画面也并不鲜见,这都说明当时对女性身体的裸露有一种正面的态度。
章怀太子墓甬道壁画《观鸟捕蝉图》 ©网络
最有代表性的唐代女性形象出自周昉、张萱笔下,两位画家创作了大量女性题材画。周昉的《调琴啜茗图》描绘三位贵妇在两位侍女的侍奉下弹琴、品茗、赏乐的场景,整个画面节奏舒缓,人物神态闲适,颇有意味的是,贵妇丰满的身形和侍女的略显瘦削形成明显的对比,这也表现出唐代对健康丰满的女性身材的崇尚。
周昉《调琴啜茗图》,现藏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 ©网络
而在《簪花仕女图》里,周昉笔下的贵妇身着华服,透过外罩的薄纱,隐约可以看到里面的纹饰,说明当时纺织技术已经非常高超。头上梳着高高的发髻,簪上缀有鲜花,并配有带流苏的精美首饰,是白居易《长恨歌》中“云鬓花颜金步摇”的生动再现。人物独特的“蛾眉”妆,眉毛前部阔,尾部短,也让人想起张祜“淡扫蛾眉朝至尊”的诗句。画中贵妇手中拈花,仙鹤、小犬环绕四周,一副闲适场面。这幅画中,无论从构图还是描绘的生活场景来看,女性都是真正的主角。
周昉《簪花仕女图》,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辽宁省博物馆
而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则描绘了杨玉环三姐虢国夫人的春游场面,整幅画作以虢国夫人及仕女为中心,男性侍从处于附属地位。这一方面是由于画中人的社会地位所致,另一方面也可窥见女性地位的提高——将游春画面作为绘画题材,也表明女性活动的空间的扩大。整体来说,唐代对女性较为包容,武则天出现在唐代,也与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密不可分。
摹《虢国夫人游春图》 ©辽宁省博物馆
「你耕田来我织布?」
今天流传下来的女性画像,多是描绘贵族宫闱生活,但仍有部分作品反映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比如劳作的场景。
张萱的《捣练图》,描绘了宫闱妇人捣练、络丝、熨平的场景,图中的女性服饰华美,神态安详,所用的地毯、火炉等器具精美异常。在熨烫的环节,一位女童穿梭在布匹之下,趣味盎然。
张萱《捣练图》,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 ©网络
但是从这幅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妇女所穿的服装如披肩、长裙,其实并不便于劳作。这样的图画与其说是对劳动场景的再现,不如说只是在宣示女性所承担的社会职责。
而在周昉的《纨扇仕女图》中,也有这样一位斜靠织床的织女,神态慵
周昉《纨扇仕女图》 ©网络
这些描绘纺织场景的画作,不过是一遍遍重复着纺织的性别属性,强化社会给予女性的身份。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还藏有一幅《乞巧图》,描绘深宅大院中众女眷向天祭拜,乞求自己心灵手巧、善于纺织的场面。画面中回环曲折的亭廊,深掩的树木,展现出“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意境,也昭示着女性深居简出的活动范围。
公元9—10世纪的《乞巧图》,佚名,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网络
宋代以来,由于科举制度推行,门阀贵族阶级消亡,平民意识逐渐兴盛,图画中对于普通人的生活记录才多了起来,比如宋李嵩的《货郎图》。画中描绘的是一个肩挑玩具百货的货郎,受到乡村小孩子欢迎的场景。画面左方有一女子抱着婴孩,妇人粗布衣衫,裹着头巾,摊开上衣正给孩子哺乳。这种展示妇女身体的场景,不是在欣赏人体之美,更多是复现生活的真实场景,古时养育孩子的任务,被认为理所应当由妇女承担。
李嵩《货郎图》,绢本水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网络
而北宋王居正的《纺车图》里,则描绘了普通农家的纺织场景,与周昉、张萱画中的贵妇不同,《纺车图》中的两个妇人合力纺织,衣服打有补丁,蓬头垢面,面露愁苦,似乎在叹息生活不易。年轻女子的怀中抱有婴儿,老妪的手臂上还能看见肌肉,说明她常年不辞辛劳。这样一幅图画,足以说明在传统社会中,普通妇女所承担的工作是十分沉重的,远非“你耕田来我织布”那么诗情画意。
王居正《纺车图》,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博物院
「多愁多病是美人」
宋代以后,儒家理学思想的兴盛,更强调男性的主导与女性的从属地位,女性是需要被保护的、是柔弱的、需要顺从的,“缠足”陋习也在同一时期兴起。在绘画中,出现了一种“美人图”,塑造身形瘦削、弱不禁风、养在深闺的女性形象。
以画仕女像闻名的唐伯虎,有一幅《王蜀宫伎图》,虽然画中人是五代前蜀的宫女,但实际反映的却是唐伯虎所处的明朝要求的女性形象,画面中的宫女身形弱小,头颈向前微倾,似乎身体难以承担头部的重量,长裙之下隐约露出三寸金莲,着装虽和唐代丽人一样华美,但早已没有了当时的丰腴健康。
唐伯虎《王蜀宫伎图》,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博物院
明清的美人图,常常将画面背景设于书房深闺之中,似乎画中女子受不得半点天风,而主人公也常常是坐姿或倚靠的姿态,以免身体过于劳累。清代改绮的《元机诗意图》,所画人物是唐代女诗人鱼玄机,因为避讳康熙名字玄烨改为了元机。图中的女诗人倚靠在树根随形椅上,身体微微前倾,双眼似颦似笑,膝上放有一摊开的书卷。
《元机诗意图》,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博物院
这幅画若不看题名,说这位多愁多病的画中人是林黛玉也没有问题,此时社会对女性的审美就是一种“病态美”了,从对“缠足”的推崇也可见一斑。
画中女性的活动范围也在缩小,从郊外春游逐渐退回室内闺阁,即便伤春悲秋,想赏玩景色,也大多只能在庭院之间,像仇英的《汉宫春晓图》、焦秉贞的《仕女图册》中描绘的女性游玩于山水庭台之间,看起来天地广阔,实际上却是人工规划的空间。女性活动空间的缩小,一方面和“缠足”后不良于行有关,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社会对女性的期待。
明仇英《汉宫春晓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网络
除了绘画中的女性形象变得固化、刻板以外,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数千年的绘画史上,知名女画家简直寥若晨星,最为人熟知的管道昇,也是借了夫婿赵孟頫的名声才为人们所知,我们只能借男性的画笔了解古代女性形象。这种现象要到近代个性解放,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女性画家如潘玉良、方君璧、孙多慈以后,才得以改观。
元代女性画家管道升所作《水竹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网络
今天,当你在这些精美绝伦的画作前流连的时候,是否透过一个个迷人的容妆和身姿,看出真实生活中,历史曾经强加给女性的身份负担呢?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我们理应为性别更加平等的社会而努力,这绝不应止于一个良好的期待。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2]巫鸿,《中国绘画中的“女性空间”》三联书店出版社,2019.
[3]纪江红,《中国传世人物画》北京出版社,2004.
文丨罗维
文字编辑丨沐钧、陈曼菲
图片编辑丨雪哥
封图丨辽宁省博物馆
本文由华夏风物原创,未经授权,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