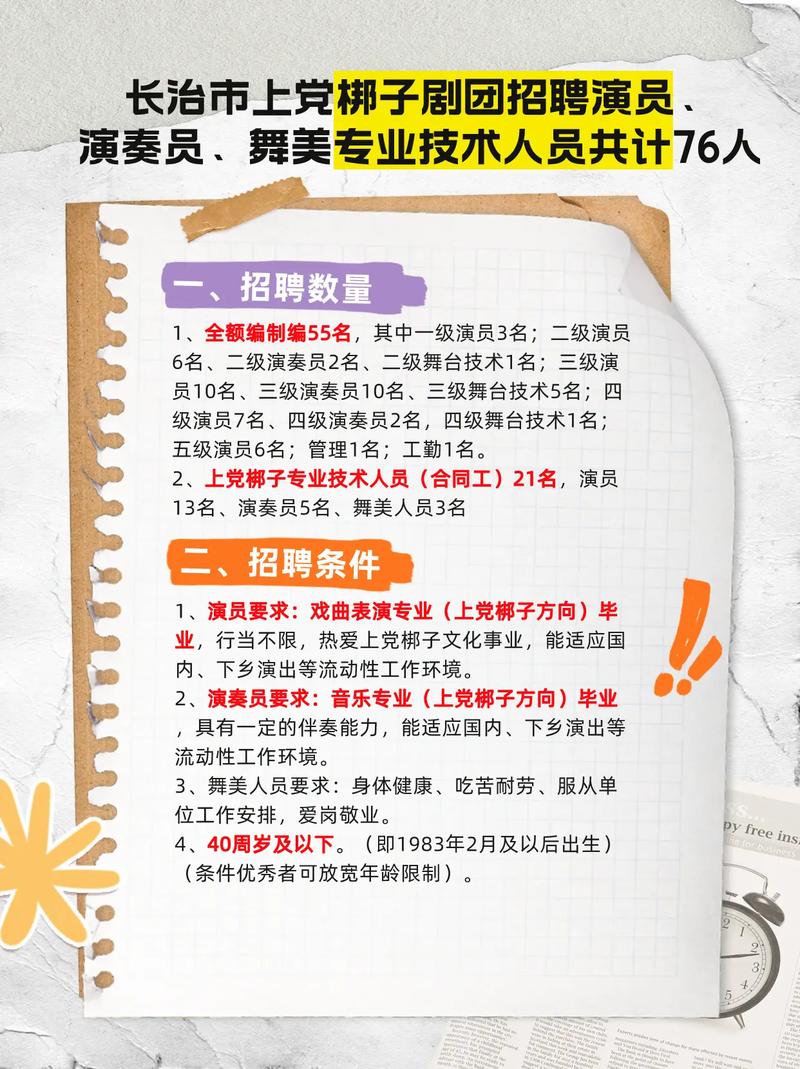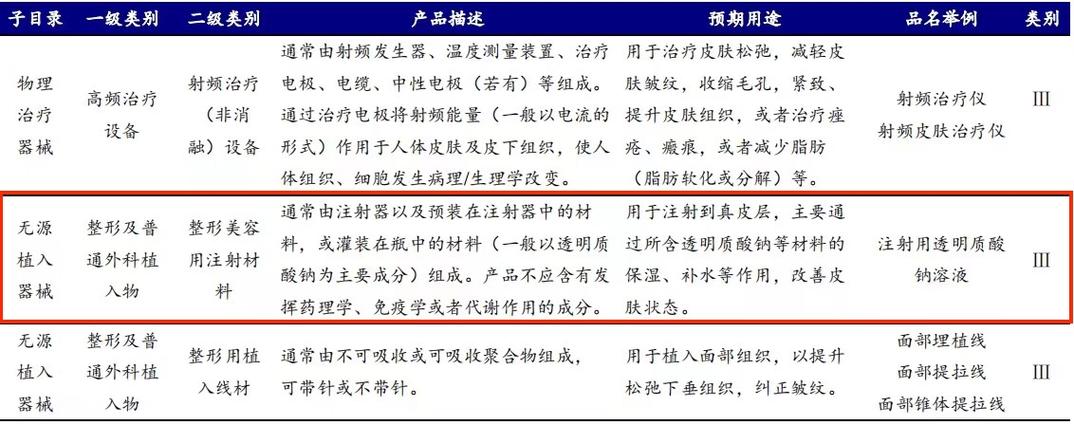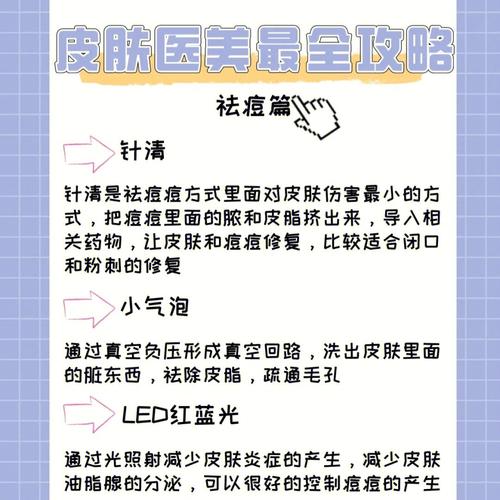乡情巢湖:有一种戏叫庐剧(劇團叔叔有一種)
听 戏 杂 感
昨日,沪上一位乡友约我去浦东塘桥听戏,便欣然前往。其实欣然的不是听戏,是去听乡音。
对于故乡的庐剧,我是既陌生,又熟悉。说陌生,是因为庐剧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喜爱,70后的大多恐怕都有此同感。熟悉它,是因为从小就在庐剧之家长大,那时爷爷还曾是庐剧团团长,姑母是从小唱庐剧的,也曾在四乡八镇红极一时:叔叔后来顶爷爷的职也进了县庐剧团,从事服装道具工作,他是不会唱的,只偶尔跑个龙套,扮个衙役、家丁什么的,喊一、二声“威武”之类的台词。

1986年,我从镇上考入市二中读高中,因离家较远,中午便在叔叔家吃饭,有时晚上也住下。那时,县庐剧团在新兴文化市场的不断繁荣中,已经日渐衰落,越发的不景气。记得剧场是位于现在安德利商场后面,边上是邮电局,对面是粮食局。叔叔和婶娘曾在剧场的道具间住过一段时间,狭小逼仄的空间里只容得下一张床和几样简陋的桌椅和箱奁,一只矮小的煤炭炉放在走道的拐角处,打发着他俩的日子,清贫中生着一丝烟火气。后来,叔叔家搬进了剧团集体宿舍。
对于剧团的集体宿舍,我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不仅是因为在那儿生活了四年,更多的是感受到那个时代集体生活中的一种非常特别的人情味。
宿舍楼位于人民路和东风路路口,紧挨着县粮食局,一楼半边临街的是药店,另半边及二、三楼是宿舍。叔叔家在三楼,只有一间房,是临街的。多数人家也都只有一间房,极少数人家有两间,想来应该是领导或“台柱子”。87年县庐剧团撤消解散时,放道具的两间房还曾引起一些不睦的口角,这也是很自然的。房间里自然是不能生火的,家家都将炉具、蜂窝煤和碗柜放在走廊上,每当饭点时,整个楼道里弥漫着诱人的饭菜香和刺鼻的煤烟气。自来水没有引接入户,只在一楼后面墙根下有一排水龙头,忙时,需要排队。每次吃完饭,我都抢着下去洗碗筷,我喜欢那种感觉,在英俊的小生叔叔和漂亮的花旦阿姨们的赞许声中,很是满足和幸福。四年时光里,他(她)们都对我十分的喜爱,当然,我也十分的懂事,嘴也甜,自是会讨他(她)们喜欢,叔叔和婶娘更不用说了。我常常回味那美好的时光,感受生活的温暖。
武生陈叔叔个头不高,夏天时喜欢光着膀子,身上的腱子肉隆起老高,时不时地会在楼道里吆喝两声,散发着勃勃生气,仿佛是要出征的将军,在校军场上点兵。他对我很好,有时也会在我面前练上两趟,招式我虽不懂,却也看出仍是戏台上的动作,不如《少林寺》里的“觉远”厉害,不过,我还是要叫好的。那时,陈叔叔好像一直单着身,也未曾见过女客上他门。其实,单身也好,挺自由的。想来,陈叔叔也是这么想的,不知他后来怎么样了,也不知他先前是怎么样的……
可能是基因的缘故吧,我一直觉得娟娟阿姨的宝贝儿子长得极像《红楼梦》里的宝玉,粉妆玉琢,一团喜气,特别招人疼爱。小家伙比堂弟还小好几岁,堂弟有时带着团里的孩子们去楼下玩耍,他总是文静的像个姑娘。记得有一次,一个叫小林子的“兄弟”将沙子放入楼下停着的一辆摩托车的油箱里,被大人们发现后,小林子像没事人似的,他竟被吓哭了。从那后,他的身影时常出现在女孩儿们中,小林子再也不和他玩了。
“宝玉”的爸爸那时是团长,后来剧团撤消了,他任了工人文化宫馆长。他是县庐剧团历史上最后一任团长,对于剧团的解散和庐剧的式微,他应该有着不一样的感受吧。
剧团虽然解散了,但宿舍还在,大家都还住在一起。一楼的赵叔叔和叶阿姨、二楼的“四妈”一家,三楼的“团长”和娟娟阿姨,与叔叔家来往的更亲近些,时常饭后在一起打麻将。在谁家打,自然是在谁家吃饭。婶娘是上海人,老三届下放到安徽,她是不打麻将的,但烧菜的手艺全团皆知,堂弟当年没考上高中,可能和她的手艺好有关。
婶娘年青时长得很好看,她看上英俊的叔叔后便嫁了,后来落实政策也没返城,只是将堂弟的户口迁入上海,自己则跟着叔叔留在了安徽。记得婶娘那时用一种叫“粉纸”的化妆品,做成最小号的电话簿样,有百十来张,用时撕下一页,既能揩去脸上的油脂,又能起到敷粉掩瑕的作用。我是偶尔偷偷用过后知道的,用过后的“粉纸”不敢乱丢,便揉成一团,扔出临街的窗口。
我经常站在那临街的窗口,望着下面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记忆最深的是有位卖草药的妇女,几乎每天从窗下经过,喊着响亮的叫卖声:“卖,淌鼻血地——方子啊”。每当她从窗下经过时,我都会被这一声“卖,淌鼻血地——方子啊……”吸引到窗前,伸出头向下张望:她的左胳膊肘上挎(kuan,四声)着一只竹编菜篮,里面可能就是那治流鼻血的草药。她长着什么样子,我从来都没仔细地关注,只是聆听她那一遍又一遍的叫卖声。
剧团解散前,还来过一位二十二、三岁的年青姑娘,她是来剧团实习的,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了。她是我那时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举手投足之间有种特别的风致,说话的声音很令人陶醉,后来看韩再芬演的《郑小姣》,便会想起她。她和叔叔、婶娘很投缘,常来家玩,有时也留下来一起吃饭。她也喜欢站在那窗口往下瞧,她站在窗口往下瞧时,我便偷偷地站在门口瞧她的背影。她转身时,我会脸红的,虽然我喊她姐姐。
剧团解散后,她便离开了,从此再无音讯……
忘记的远不止这位我叫她“姐姐”的年青姑娘的名字,李道周、李乐群,洪桂兰、徐敬斌,郑静荣、水曼莉、谢昌琴、汤文英、汪华、方玉霞、宋忠武、毛明玉、王仁标、石云、王寿山、芦苇、马长才、蒋光玲、武道芳、王治才、方世才、孙家茂、曹明胜……等一大批当年活跃在庐剧界的名耆,除了姑妈和她的几位常有来往的好友外,大多已从脑海里消失了,若不是查阅资料,可能再也想不起这些名字。
朱鹤年老先生在《不解的情结》一文中曾用这样的文字来表达他对庐剧的钟情和感叹:“当台上的洪桂兰和白发飘飘的郑静荣在演出中流下泪水时,台下人无不为之感动。说真的,我的感动,有剧情的原因,但更多的成分却是被这些庐剧的挚爱者们这种执著的精神,这种不舍的情怀,所深深感动!
依稀的色彩,依然的鼓乐,依旧的故人,使我逆返时空隧道,重新造访四十年前。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我曾多次怀着欣喜的心情欣赏过一如今天的剧目。我曾一再地为台上的演出而深深地感动过。那时候,有多少名字和形象,曾令巢县人为之销魂!
”
朱老先生的感慨,今日不知还会几人有。往日的色彩,往日的鼓乐,往日的故人,往日的泪水,往日的许许多多,不知明日可还有人来忆……
黄梅戏曾因电影《天仙配》红遍全国,越剧也曾因电影《红楼梦》为世人所知。若不是十年文革之故,庐剧《陷巢州》也会被搬上银幕,传唱天下,那么庐剧的命运一定会是另一番景象。正如方晗老师在《大红大紫一出戏》(追忆庐剧《陷巢州》台前幕后)中所言:“巢县庐剧团以一部自创剧目征服了千万观众,树立了自身品牌,创造了惊人经济效益,同时也宣传了巢湖。《陷巢州》这部戏是地地道道‘巢湖的土特产’,它取材于巢湖民间传说,取景于巢湖的山水风光,取曲于巢湖乡音民谣。它的成功就在于它的独特,浓郁的地方特色是其永恒的魅力。”
当年,刚解禁的越剧电影《红楼梦》正在全国放映,合肥观众评价说,庐剧《陷巢州》的“玉姑哭潭”,超过了越剧《红楼梦》的“宝玉哭灵”;还说巢县的《陷巢州》可与杭州的《白蛇传》相媲美。江苏广播电台、安徽电视台曾多次录音、录像播出,有的选段被安徽广播电台作为保留节目长期播出。全剧或选段还分别出版了不少盒式音带,多首唱腔被收入《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安徽卷》。
戏曲属于舞台,却要借助银屏发力,这是时代变迁的结果。马路还叫马路,上面跑的却是汽车了。戏曲电影虽然利于传播,但总不如舞台上真人瞧得分明,空气中传来的是现场的一咏一叹,鼓乐声中,有着艺人们铿锵的动作,水袖挥舞间,有着角色的舞台人生,台下的唏嘘声会和着台上的悲腔调,形成强有力的感染力。就连走台、唱词中的即兴应变和补救,有时也会成为观众评头论足的佐料。二维的空间总是没有三维的世界显得那么真切,看戏,还是坐在舞台前的好。
2008年,由李道周牵头,原巢县的一批庐剧精英们发起成立了“巢湖梨园剧社”。目的是抢救巢湖地方文化,振兴传统戏曲艺术,发现培养庐剧新秀,繁荣群众文化生活。李道周的家也因此成了剧社的主要活动场所,他们因陋就简,排了一些庐剧折子戏,到群众中演出,大受欢迎。夕阳无限好,为霞尚满天——这是庐剧界老一辈们的朝阳重升,春芽新吐。
李道周是国家二级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安徽庐剧四大名旦之一,也是庐剧中路代表人物。1953年进巢县庐剧团时,她还是个19岁的初中生。她自小酷爱戏曲,天生一副好嗓子,加上天资聪慧,勤学苦练,在剧团迅速成长为头牌花旦。先后在《红楼梦》、《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江姐》、《陷巢州》等数十部戏中担任主演,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早在1956年,由她主演的庐剧《拾金钗》代表芜湖专区代表团参加安徽省“第一届戏曲汇演”,就一举夺得了二等奖。她的演唱清新甜美、流畅自然,嗓音细润舒柔,吐字清晰,能高能低、能细能厚,韵味十足;她扮相俊俏秀丽,气质温婉,表演含蓄传神,善于描摹人物神态,细腻刻画人物内心世界,举手投足恰到好处,动作自然到位而不造作,一个转身一个眼神,都给人无限的美感。许多年里,只要中央首长来巢湖,招待首长们观看李道周庐剧折子戏是重要保留节目。刘伯承、郭沫若夫妇、李克农、万里等领导,都曾兴致勃勃地观看过李道周演的庐剧,并给予她很高的评价。
当年李老在《陷庐州》“哭潭”一场戏中,只配一把二胡,上台时她一声“哥哥”呼喊,全场观众的心随之一揪。“遍寻哥哥哥不在,只见碧血染苍苔,哥哥果真遭残害,哥哥啊,怪不得我盼断肝肠不见你归来……啊,哥哥呀!
我千呼万唤无人应,力竭泪尽不成声,龙潭纵是黄泉路,也向潭底把哥寻……”那字字血声声泪的呼唤哭诉,凄婉哀切,撕心裂肺,曾使偌大的剧场内一遍唏嘘,所有的观众都被她带进剧情中。可见,被称为“倒七戏”、“小倒戏”的庐剧,在当年也曾红冠一方。
2012年,在企业家孙德惠的劝说和资助下,洪桂兰和徐敬斌夫妇又成立了“巢湖市兰兰庐剧演唱团”。4月20日在原居巢区政府会场揭牌,填补了自1987年原巢县庐剧团撤消后,巢湖市长达25年没有专业剧团的空白。孙老曾告诉,下一步他希望能够解决兰兰庐剧团的后继人才补给问题,通过老艺人的传帮带将庐剧艺术发扬光大,为群众送去喜闻乐见的文化大餐,也成为城市的一张文化名片。
后继有人,发扬光大。这是所有艺术门类的生存之道和共同所愿,也是无数将一生奉献这项艺术的老一辈们的毕生追求。艺术若是青山,他(她)们便是那长流的清泉。
最忆是巢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