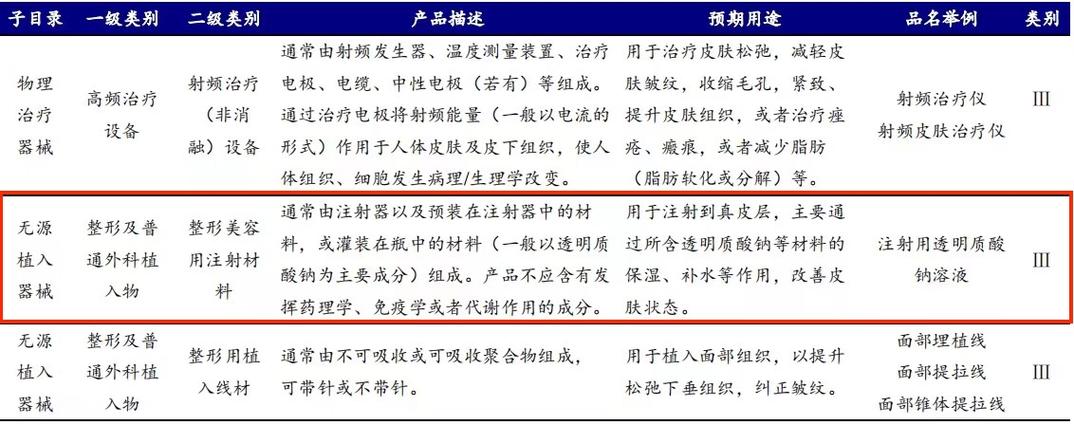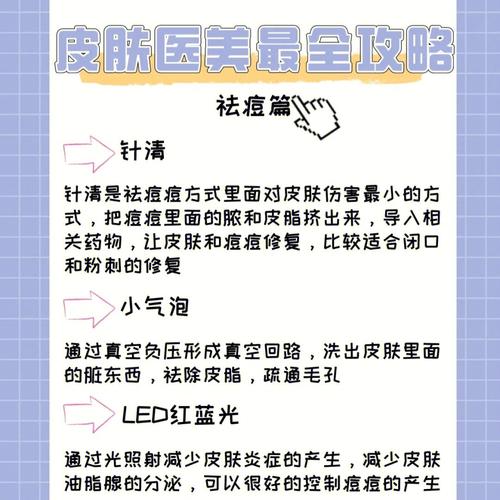宋琳:《山海经》传 |《草堂》头条诗人(山海經神話我是)
宋琳,1959年生于福建厦门,祖籍宁德。1983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91年移居法国,2003年以来受聘于国内几所大学执教。现居大理。著有诗集《城市人》(合集)、《门厅》、《断片与骊歌》(中法)、《城墙与落日》(中法)、《雪夜访戴》、《口信》、《宋琳诗选》、《星期天的麻雀》(中英)、《兀鹰飞过城市》、《采撷者之诗》(英文);随笔集《对移动冰川的不断接近》、《俄尔甫斯回头》等;编有当代诗选《空白练习曲》(合作)。《今天》文学杂志的诗歌编辑。曾获得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奖、《上海文学》奖、东荡子诗歌奖、昌耀诗歌奖、2020南方文学盛典年度诗人奖、美国北加州图书奖等。
西王母之邦赫然在目。
诗 艺 宋 琳
”
驺虞又有什么稀奇?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我生活的信条,
当观看的人齐声喝彩
是的,即使在隆冬,
开渠呀!
诗是对诗的纪念。诗歌写作本身是纪念性的,既对于往昔的诗歌,也对于匆匆岁月。诗人似乎怀有让时间停止的梦想,或者可以说,诗人通过严肃的写作与时间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游戏,直到某一天发现头发斑白了。由于这一小群人对世界的爱的固执,他们的精神贡品有朝一日会成为新的纪念物。
三种时间中的过去时间并未完全逝去,它在我们的记忆中若隐若现,以回声的方式作用于我们,记忆者的回忆就是返回并抵达那个泉水丰沛的神秘地带,中国先哲将它命名为“泪谷”,希腊人称之莫涅摩辛涅(Mnemosyne)与厉司(Lethe):记忆之泉与忘川。记忆或遗忘皆难解之谜,传说古希腊的求神降示者必须喝这两条山泉的水。博尔赫斯曾写下一句奇怪的诗:不存在的事物只有一件,那就是遗忘。为什么说遗忘是不存在的呢?或许因为人本质上总是不停地在回忆,在缅怀。诗人的怀旧式情感如此浩大,以致于必须发明出“万古愁”这个词来承载。我想,所谓宇宙灵魂、天地之心所指都是同一个东西,它收留并保管着我们个人的记忆。
来自生存的和精神的双重危机,考验着当代诗人的勇气和耐心,他在心中呼唤着“作为内在凝思和经验保存”的记忆王国(一个并不存在的国家)的降临,作为此呼唤的应答,记忆女神摇身成为他的保护神,道路之神经常给予他引导。
处于悬空状态的精神必须重新赢得栖居之地,而写作,正如阿多诺所说,将成为此栖居之地。一方面是本土经验的内在记忆化,一方面是诗歌地理空间的拓展与陌生化的持续需要,经验的主人感受到断裂和新的撞击;记忆者意识到自己是母语的携带者。写作,倘若未曾认清母语的遗产,就有可能再度落空。
精神的缺席可以这样来理解:一个被耽延的尚未现身的“现在”遮蔽在不准确的写作行为中。诗人的词语是时间和生命的混合物,对于精神与历史及时代的关联,我尚未找到比招魂术这个词更贴切的比喻,诗人的漫游或许有可能获得破译不同文化语符的仪式道具,而写作者文化身份的重新确认,则几乎是一种自招其魂的开始。
处于崇尚物质主义的、灵肉分离的时代,诗更其作为挽歌——对逝者,对曾经有过的精神完整性的招魂。诗是挽歌,所以诗歌艺术是一种招魂术。《易》有游魂、归魂之卦象,可作万物之灵皆合于阴阳变化解;《楚辞·招魂》本于楚地的民间习俗,而招魂仪式在一些南方省份至今犹存。司马迁描述此习俗时认为是生者对临死状态的人所作的挽歌:“精神越散,与形离别,恐命将终,所行不遂,故愤然大招其魂。”《招魂》诗中的主体巫阳无疑堪与希腊神话人物俄尔甫斯相媲美,属于原创诗学意义上的中国诗人原型,她对着冥界歌唱,招唤死者返回,将语言化作无限凄美的祈祷,亦是通灵者的一种越界的对话。
另一种唱给自己的挽歌,同属有关终极事物的最后的言说,与“先行到死亡中去”的存在主义诗学不谋而合,将死亡事件引向天人之际,可以说是招魂诗的变体。
当代诗因太多的否定因素,常常如燕卜逊所说:“不过是一场鬼脸游戏”,或许是时代本身的否定因素使然。语言的接力据说发生在三五年之间,三五年为一变。我不置可否,但乐观其成。然我终不是文学史家,就当下而言,没有极深研几的识力无从谈变化。语言的变化绵延不尽,与世代相颉颃,“变风发乎情”这一儒家诗学言说虽古拙,却并未过时,诗人之情通乎世情,世情所迫,“诗变”乃不得已而发生。如此演绎虽只是常识的重申,亦可理解为从常识出发的一种敦促。然“天不变,道亦不变”,诗歌不会因形式的变迁而放弃对心灵守护神的召唤。
为了更好地纪念诗歌这种久远的文学类型,一种对重返精神原乡的诗歌写作的期待,已然要求诗人们超越日常生活的散漫无序,同时避免过度的精致化,在个人记事中观照历史,又从历史诗学中参透现代感性;不是带着恋尸癖般回首的遗憾,而是将“原始灵视”(荣格语)的修为当作朝向终极性之一瞥的日课。那么,避免毁宗庙之事重演的当代忧虑或将帮助我们度过更大的危机。“人心维危,道心维微”,深于诗者,其见天地之纯乎?
神话的重写与我们
——读宋琳《<山海经>传》
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应该如何面对那些上古的神话?自神话学建立以来,各种研究模式为理解那样一个神人混杂的世界提供了思路。人类学、心理学和结构主义的方法被运用到神话研究之中,解答了诸如神话为何存在、神话的功能、神话与历史的关系等问题。理解神话,某种意义上,就是为几千年的古代人确定一个文化框架,在这个框架中,生殖、饮食、死亡和暴力都各归其位。但不论哪种思路,神话都是以适当的工具去剖析的对象。我们希望理解神话,但充满悖论地与之保持距离,方式首先是使神话变得陌生。古代人和他们的作品,模糊为一个可供遥想的远去的世界。很少人会相信古代人值得严肃对待,就像谈起他们时,我们总是会带上一句“那不过是神话嘛”。正是这种疏离感,界定了我们与古代人之间的差异,而由于受到了进步主义的加持,它有增无减。进步主义者认为,几千年以来,我们的文明和意识早已今非昔比,文明是累加和进化的,就像历史教材中的猿人必将褪去遮羞的树叶而穿上绅士的礼服。在中国,由于受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影响,对古代世界的想象更凝固为某种“装置”,主要特征是“野蛮-文明”“低端-高级”等层次的划分。我们口头上承认古代人是祖先,但在脑海中,他们永远是一群未开化者的形象。古代神话被看作是不发达阶段的产物,文明发蒙期的酸涩果实。
这是我们如今理解古代和神话的普遍意识,也构成了诗人宋琳重写《山海经》的语境。众所周知,《山海经》成书于战国时期,是中国上古时期最重要的一部神话,但怎样看待它的性质,历来众说纷纭。作为一部神话,它的可靠性并非不言自明,一如上文所述,随着时间向“现代”迈进,《山海经》及其背后意识的可信度也直线走低。《山海经》中有大光怪陆离的神仙,有龙身人面、人面马身、人面牛身等,这些半人半兽被认为是古代人的幻想或早期思维的投影。鲁迅就曾将《山海经》定性为“巫书”,一部宗教和仪轨的记录,书中的奇怪形象则折射了古代人的宗教意识。以刊登于本卷《草堂》的《<山海经>传》选章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宋琳为如何理解神话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在这种思路中,神话对于我们来说不再是对象性和工具性的,面对那些半人半神,我们不必汲汲于从中解读象征含义。当诗人用现代汉语加载起古代神话后,时空阻隔造成的疏离感消失了,代之以一种“共同感”。宋琳的诗提醒我们,或许现代性膨胀的假象远远夸大了我们与古人的距离。于是,神话不再是有待处理的文献,我们可以与那些神人怪来一次贴面拥抱,就像是推心置腹的朋友。很大程度上,宋琳对《山海经》的重写是对“现代优越感”的克服,读这些诗,应该没有人再会对古代人侧目而视或露出鄙夷的神情。这是因为,在情感、伦理和精神意识的层面上,我们仍与他们保持着一种难以割舍的亲密。在神话与我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宿命般的联通感,只不过我们并未清晰地意识到。
“少昊”是《山海经》中一个经历了颠沛琉璃的人物。他在东方的海外统治一个鸟的国,而他自己本身也是一只玄鸟(即燕子,玄鸟在后来的神话著述中演化为凤鸟)。少昊从东方转移到西方,并被称为“白帝少昊”,先是担任山神的卑下职位,之后始料不及地加冕了西方的天帝,可称得上是“大起大落”。少昊的身世为人津津乐道,他的母亲在穷桑之地邂逅了一位太白金星的天上仙童,两人泛舟遨游,赋诗唱答,于是上演了一场浪的恋爱,生下了少昊。《少昊》一诗就是宋琳对这个人物的重写。在重写中,他基本上抓住了包括少昊的诞生和执政的原型框架,并对尚未确定的细节持“保留意见”。实际上,少昊诞生的情节并非直接出现在《山海经》中,而是东晋时期的志怪小说《拾遗记》所记载的。这说明,仅仅研读《山海经》还不够,动笔写作之前,宋琳必须要对《山海经》及其衍生和研究性著作有广泛的阅读。据神话研究者袁珂的考证,少昊母亲的身世在现有的文献中似乎还没有找到确切的说明,相应地,宋琳在诗中保留了这样一笔:“但我母亲的高贵血统/却有待考证。”在《<山海经>传》中,代入人物内心的独白发声是重写的主要的方式之一(下文会有详细的讨论),但类似“有待考证”的研究性笔触时而旁逸斜出,逾越于独白之外。再举一例,在《壤夫》一诗的前面,以壤夫老人之嘴说出这样的句子:“未来将有一个叫田俅子的人/写下这奇事,而它正是历法的起源。”田俅子即田鸠,庄子的同时代人,他收录在《汉书·艺文志》的著述对《山海经》中的“壤父”故事有所扩写。将对神话的说明插入到神话人物的独白之中,或许破坏一首诗的整体观感,但宋琳还是保留了下来,我们从中能侧面看到一种严谨的态度。此类”限制性说明“暗示读者,《<山海经>传》尽管取材自神话,但都有据可循,绝非信马由缰的幻想。可见,宋琳的重写铺开在一个可靠的基础之上。
《山海经》中的半人半兽很少单拎出来描写,而往往出现在故事之中,作为叙事的“符码”而存在。他们的形象光怪陆离,行为举止也令人惊叹。不过阅读神话还是迥异于小说,在神话那里,人物作为叙述符码或象征符号不存在可体察的意识。与此同时,我们也很难想象这些“怪物”会拥有像我们一样意图、精神和情感。这或许缘于我们对整个古代社会的认识:由于生产力低下,先民们对自然不具备开发能力,而他们像婴儿一样,与世界也处于一种混沌未分的状态之中。换句话说,清晰的自我意识还未分化出来。真的是这样吗?《山海经》确实鲜见对人物心灵的描摹,然而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心灵。当少昊的母亲与年轻的恋人坠入爱河,虽然寥寥数语之中没有关于他们激情的描写,但结合本身已经说明了心灵的碰撞。同样的,少昊的迁徙和地位的升降,尽管缺少心理描写那样内化的说明,但我们就能漠视他的痛苦吗?这其中的道理是很明显的,甚至都用不到任何理论的说明。正是在古代人所拥有的活跃心灵与我们并差异的意义上,宋琳对《山海经》的重写是成立的。《少昊》一诗最出彩的地方,就在对“迁徙”的阐释上,宋琳试图去理解少昊在从东到西,从高贵到卑微的转移之中的复杂感受。通过阐释性独白,他想象性地代入少昊本尊,以便透过心灵去理解那一段叙述:
不如说我是双重性的儿子。
我身上集合着两种相反的本能:
结束或开始,如黎明与黄昏,
群星皆暗时我最亮,
我导航,调理着四季的风向。
(《少昊》)
“双重性的儿子”、“两种相反的本能”当然不像是古代人会说出的,但这不妨碍现代汉语在处理神话人物的有效性。使用这样的表达,宋琳试图将古代人的心灵处境转化到一个亲悉的语境中。稍作联想,少昊也“照映”着我们,在他的迁徙和现代中国的文化遭遇之间,精神处境的相似性显而易见了。现代中国正是在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双重性”之间挣扎生成。离开这种“双重性”而固守一方,我们几乎难以想象自身。根据学者朱大可的研究,《山海经》是一份典型的“全球化”文献,经过考察,书中形形色色的地理和动植物很多在域外才能找到。当时的古人如何能掌握来自全世界的知识呢?朱大可认为,要是上古中国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社会,这些内容就根本不会出现,只有置身于全球规模的人口流动之中,《山海经》才有可能采集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博物知识。《山海经》是否是“交互原则”和“全球化”旅行之后的产物当然还有待细究,不过,像少昊这样带领部族大跨度的迁徙在中国史上是很普遍的。当人不得不放弃“旧居”去寻找、适应新的生存空间和文化气候时,心灵的波动也随之产生。值得一提的是,宋琳本人也有漫长的海外旅居的经历,曾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游历,对于少昊的迁徙,他或许更是心有戚戚。
根据荣格的看法,人生有多少种典型的情景就有多少原型。神话世界尽管光怪陆离,但它们作为“集体无意识”仍然潜藏在我们的深处。人格结构并非单纯可见,在自我意识和潜意识背后,还有更深层的集体潜意识,后者是一个民族世代活动的方式和经验库存的遗迹。几乎不须经验的帮助,个人的行动就和他的先人之间有某种相似性。神话与我们的密切在于,它以故事和“原型”表达了我们的梦想。荣格的理论解释了追溯认同的一部分理由:当我们认为属于谁的后代时,并非仅从生物学上确认相似,更多是从精神的脉络之中寻找凝聚力。比如“蚩尤”,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神话人物,他与炎帝本属同一个部落,因矛盾而“单飞”自行发展。蚩尤为人所记,主要是因为他与炎帝和黄帝之间的大战,而后两者构成了与中国人“炎黄子孙”的认同的神话基础。《山海经》对蚩尤的叙述相对简单:黄帝派遣部下应龙去抵御蚩尤,应龙使用水战,但蚩尤请来了操纵风雨的巫师制造了特大风暴;最后,黄帝只能从天上派遣女儿“魃”下来止住风雨,擒杀了蚩尤。在之后的一些注释性的著作中,细节有所增加,但叙述的框架没有变化。宋琳的《蚩尤》一诗对这段神话来了一次完全抒情化的演绎。诗句精短而具有活力,如同宣告,以蚩尤第一人称的独白讲述战斗的经历。于是部族间的争执退居背景,战士的勇气在鼓声中开始彰显:
我们终于直接听到了战士蚩尤的激情,而不仅仅是在故事中认识他。“四目六臂,头上长角”是奇异的相貌,但不显得狰狞可怕,蚩尤本尊对自身的描述让它成为了英勇的象征和骄傲的确认。“来呀,指南车,/来呀,熊罴䝙虎,/来尝尝我飞空走险的铁蹄”,连续的呼告是战斗前充满挑衅的宣战。由于“炎黄”的正统性,不少儒家士大夫在评注蚩尤的时候,一方面从相貌上丑化蚩尤,另一方面,把他当作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一类人物,比如在《书·吕刑》中就有“蚩尤惟始作乱”的评价。但我们完全可以扫去历史的积尘,像宋琳这样,直击蚩尤作为战斗者的心灵。拨开所谓“正统”和“道德”的烟雾,我们也能看到另一种充满战斗性的、反叛者的尊严。如果稍作引申,这种反叛的尊严,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之间也有着可比拟的精神线索,它们都是英雄主义的赞歌。
宋琳对《山海经》的重写并不遵循任何统摄性的观念,而是让神话及其人物自身显现。像历史学家那样褒贬或点评是画蛇添足之举。把神话人物放在平等的舞台上,他们都拥有充沛的灵魂,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类似“复调”的效果。我们既能读到少昊的纠葛,也能看到蚩尤的英勇,既能看到为荣誉而追求的进击,也能听到醉心于漫游的歌声。他们拥有独立的声音,诗人的工作,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他们各自存在的权利上色。在《脩》(xiu)一诗中,脩终于摆脱了父亲的“阴影”,找到了自己践行人生的方式。脩的父亲是共工,一位水神,属于炎帝一族,在《山海经》等书中是以叛乱者形象出现的。共工在黄帝的继承人颛顼治世的时代反叛,愤怒之下头撞不周山,造成世界向东南倾斜;之后他作为水神作乱,引发滔天的洪水,于是大禹出马,有了我们熟悉的“大禹治水”。对于父亲因渴望权力和地位而造成的生灵涂炭,脩感到心痛,他的理想则是“像夜游神那样走遍大地”。作为一个世界的漫游者,脩所仰仗的一个是爱(“难道不值得将这爱与死的范例,/传扬给谨小慎微、不敢去爱的人吗?”),一个是自由。当他撇开政治的束缚启程之际,对前路没有丝毫犹疑:
《风俗通义》中如此描述脩:“好远游,舟车所至,足迹所达,靡不穷览,故祀以为祖神。”脩放弃了神的地位而向往凡俗流浪的生活,从这里也能看到古代神话中存在的“人神无二”的事实,等到我们更为熟悉的“牛郎织女”那里,神与人的界限在张力中也模糊难辨了。就此而言,神话中虽然多是神怪,但他们在情感和心灵上是属人的。透过博览万物的浪漫事迹,宋琳在诗中为这位浪漫者的心灵赋形。在现代生活中,“行者无疆”的勇气确实是失落了,放弃有地位的或稳定的生活去全世界漫游,对我们来说很难想象了。不过,这种源自上古的渴望依然潜藏在我们的意识深处,常常在在诗歌、文学和艺术中暴露出来。就这个层面而言,神话并未随着古代的逝去而消失。
在诗集《<山海经>传》的序言中,宋琳解释道系列写作的初衷:“古神不死,在人为人,在物为物。但郁而不发非神韵不在,而是人远离了灵枢。诗作为祷歌与巫咒,庶即可以在回溯中去接引失传的古人之大体。”如果说,这种“接引”可以激活那些浪漫的古代精神,那么它也能“六经注我”——激活我们自身。我们与古代人的关系不仅是概而言之的“认同感”,更是与勇气、自由和爱等伦理性的主题相关。换句话说,在古代神话与我们之间有一种辩证的关系。就像宋琳对《山海经》的重写,一方面,他把人物从碎片和尘埃中解放出了出来,让他们自由纷呈地诉说。另一方面,这种解放也是对我们自身的重新发现,好像我们心灵的暗处也闪耀着簇簇神性与浪漫之光。所以当重新理解了神话之时,也就是重新理解了我们自身。
编辑:王傲霏,二审:牛莉,终审:金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