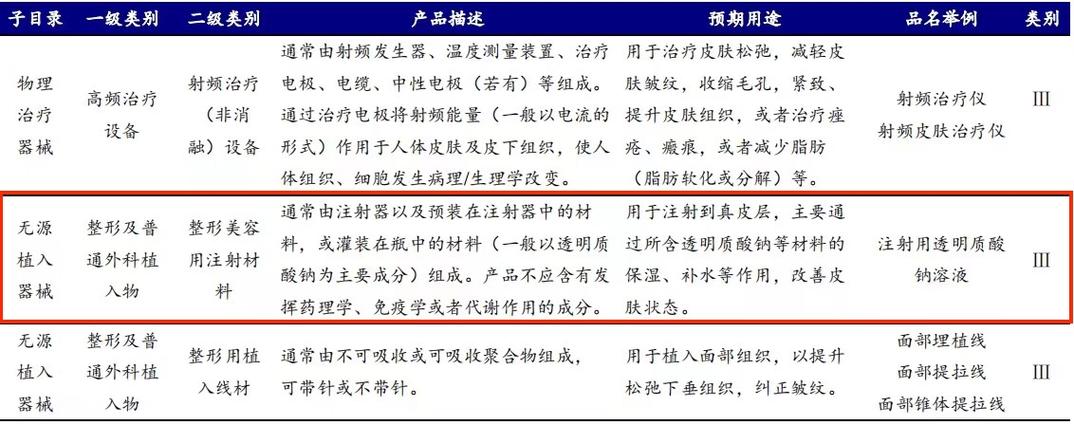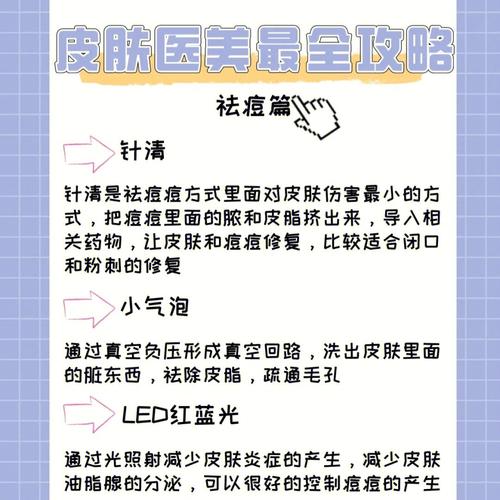话说美仁宫(胡須媽祖榕樹)
如果您满意于下面的图文,请让更多的人关注“鹭客社”。
回望美仁宫
一首旧时的厦门民谣以小城各个角头、地段的行业特色,描绘出一幅风情十足的厦门《清明上河图》,而此其中小小的一块美仁宫地盘居然出现了三四处(请用厦门话念):“……将军祠曝米粉、西边掘土笋、袁厝咸菜帮、后保讨鱼罾、前保浸大蛏、美仁宫车公司、豆仔尾卖故衣、浮屿角刣大猪……”

厦门人都知道“美仁宫”。但今天大多数的厦门人仅知道“美仁宫”是一个地名。“美仁宫”成为一个地名,完全是因了那座文革中被毁掉的社神祠堂“美仁宫”的缘故。在社神祠堂的“美仁宫”诞生之前这块地盘叫“尾头”,尾头社的简称。尾头社的由来很简单:它就依着筼筜港南岸那座有点高度但在别处根本算不上山的尾头山(这山头上早年前建厦门第一所“职业学校”,这条路至今乃叫“职业路”。厦门建市之后“职业学校”外迀,此地设“郊区公署”辖全岛农村,史称“区署”。1949年后改为解放军卫生队部再改为“军队干部休养所”)。尾头社的“前社、后社、袁厝社”旧称“前保、后保、袁厝角”,一并号称“尾头三角头”,尾头人自称、互称“咱社里人”。当那座侍奉大道公、妈祖婆的社神祠屹立在尾头山东南坡上的时候,以“里仁为美”之意,取名“美仁宫”。从此,俗称的尾头山便有了雅号“美头山”,尔后“美仁宫”优雅地取代了“尾头”的地名,以至于在已经没有“美仁宫”社神祠堂的今天此地仍叫“美仁宫”。有意思的是,许多土生土长的厦门人竟然一直误以为此地芳名是“美人宫”,叫出口来有些柔情蜜意。
顺带说明:“尾头”二字的正确发音与厦门传统叫“江头”的发音一样,“头”不念“桃”而念“讨”。这个发音与至今厦门禾山人依然保留的古老的厦门话是一样的。我以为,早先“尾头人”讲的应该就是这种最老资格的渔农时代的厦门话(例如:猪叫读、鱼叫胡)。而今天厦门人所讲的已经是工商时代的厦门话了,它融合了漳厦泉的闽南语言再加些外来的洋人词汇,成为最年轻最有代表性的闽南话。
以现代厦门的地理形态来想象原先的美仁宫这片土地肯定没有头绪。那时候,今天的厦禾路美仁宫这一路段是龙船河。后江埭、西边社的溪流在此聚汇成河缓缓流淌,在兜仔尾(豆仔尾是后来的名字)注入筼筜港。龙船河年年端午龙船竞发。河的南岸是叫“后河仔”的河滩,再往南,站在“溪岸”可以望见南边一片溪流交织的阡陌,此地1927年建成了“中山公园”。传说宋代的朱熹来到厦门岛曾经站在白鹤岭上眺望尾头社,这位中国文化史上地位在三在四的贤人,对着筼筜港湾里尾头社渔人驾船撒网出没风波的景象,不禁赞叹:“万代渔翁!
”
圣贤开口也并非句句是真理。尾头人的渔事说断就断,四十年前筼筜港截流围垦,尾头社渔民这支“尾头海军”变成了“陆战队”,洗脚上岸拔鹿角——拉板车。靠海则渔,沿河耕种,地理条件决定着生存方式。20世纪初厦禾路修通带来了比种菜更有效益的商机,龙船河沿岸的菜农大多成了小商贩,仅有少数人不改初衷坚持种菜,第二市场边上那片菜园直到60年代才征用建了电机厂工人宿舍,而袁厝社四孔井、三孔井中间那片菜地则耕作至文革期间。改革开放前,厦门人说“尾头再过去就是山场(禾山农村)”,那几处种菜的保留地便是明证。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我开头就说的,旧时设立的辖区涵盖了厦门岛全部农村的“禾山区公署”就建造在职业路尽头的美头山上。
民谣总是简约而又准确了地概括了一方土地的风情。袁厝人杂姓而居,多为商贩走卒、手工艺人和菜农。“袁厝咸菜帮”,袁厝人以腌制咸菜而著名,大缸大桶里芥菜层层加盐,并以石块重压,咸菜成熟时日黄汤满溢,半丬社里香酸飘扬。很可惜这一“民间手工制作食品”绝迹多年了(吃了当今以化工手之泡制的咸菜,老厦门人忽然很怀旧)。
“后保讨鱼罾”,以宗族聚居的陈氏后保人绝大多数是渔民,捕鱼捉虾,布石种蚝,冬天拖浒苔,夏日洗虷仔(外地人称之“海瓜子”)……今天繁华商业街禾祥西路从市府大道至美仁新村这一带,原来是后保渔人的“舰队锚地”。时过境迁,沧海桑田!
“前保浸大蛏”,前保人较后保人姓氏多,可能因临近厦禾路经商者也较多。“铺面蛏、浸水蚝”,民谣仅能取有韵脚的“浸大蛏”形象地对“变小为大”的商业行为一言以蔽之。其实美仁前社人脚功制作的白生生、小圆圆的芋艿“脱白芋”也是全市闻名的。
“美仁宫车公司”,大概连相当多的老厦门都不知道,厦门最早的汽车运输公司就在美仁宫路口隔着厦禾路的那座后来改作“双全酒家”、再改作“太白酒楼”、又再改作“国记酒家”、最后被拆迁的二层楼房。后院的一片空地即是当初的停车场,后来这里变成酱油厂放酱缸的场地,绿蝇嗡嗡。原地在今冠成大厦民居楼正对面。
紧挨着美仁宫西边是豆仔尾(兜仔尾,即海湾转角处),“豆仔尾卖故衣”,这里曾经聚居着一帮在浮屿卖旧衣物的人,故有此说。这是捎带的话,与“美仁宫——尾头社”已无直接干系了。
不知是在哪个年代,哪处竹林掩映了哪一片渔火,启动了哪位诗人的灵感,“筼筜渔火”成为厦门八大景之一景。凡是有些历史的地方便会有传奇的故事。传说,大道公,妈祖婆五色宝船七彩旗巡视筼筜港,大群神圣的“妈祖婆鱼”——白海豚一路尾随,浩浩荡荡;传说,1959年那场特大台风席卷厦门岛,一夜之间掀房倒树、车毁船破,而尾头社居然无大恙,全是仰仗了陈元光的神兵神将顶风冒雨来庇护。老人们斩钉截铁地说,亲眼见黎明时分海尾仔漫漫一片红旗呼啦啦迎风挺立,“王爷公陈元光”率兵马筑成了铜墙铁壁!
又传说,乾隆皇帝巡视江南曾经圣船入筼筜,吃了本港的一种体肥厚肉细嫩味鲜美的鱼,大叫“ok”,圣上仁慈,不忍全食,特留半边投海放生。因此,至今那叫“皇帝鱼”的“贴沙比目鱼”就只敢长半边脸,顶着两只谢圣恩的小眼睛,咧着歪嘴作永远微笑的幸福状;再传说,袁厝的原住民袁姓一族因参与郑成功的反清复明活动,清兵破城后被人尽杀、屋尽毁。尸体集中填埋于袁厝小山顶,冤魂啼号故而建造袁厝土地公庙以镇之。后来杂姓人家进住袁厝,建屋大都就地掘土夯墙,墙面上瓦砾碎砖红斑点点,人们说那便是袁氏族人的血渍;最后传说,尾头社地下埋藏着十六个宝窟,不是太平军便是小刀会的遗产,还有十四个未曾破获。而破获其中两个的宝藏的幸运者也确有其人。他原先种菜于美头山上,一段时日见兽害夜夜发生,决心除害。彻夜潜伏,黎明前见有两匹似马非马的白色怪异畜牲飘然而至,奋力追逐之下那两怪物悠然入地。挥汗挖掘虽兽毛半根未得,却有白银两瓮喜出望外。这是多么诱人的、值得守株待兽的美梦啊,一想就叫人要捶胸顿足!
还有的十四个宝窟,你在何处躲藏?
“美仁宫”三个字贵为地名,在厦门市政建设的规划蓝图里肯定是永远抹不去了,但那座真实的“美仁宫”只是历史记忆中的庙堂。尾头社三角头原先有几处社祠、庙宇:后保“王公宫仔”、“武府宫仔”;袁厝“土地公宫仔”和前保的“美仁宫”。而海尾仔的“谢妈宫仔”专门收容海上飘零者的骨殖,安顿无主的野鬼孤魂。如同厦港沙坡尾的“谢妈宫仔”,地处海港岸边这一类的“阴间慈善机构”是不能没有的。
“王公宫”也叫“圆海宫”是后保人的宗族祠堂,敬奉先祖开漳圣王陈元光和天后海神妈祖婆。传说几百年前的一次九龙江大水把圣王的木雕神像带到筼筜港边的后保社海滩,社里人诚惶诚恐地抬回来,经过认真严肃有效的验证之后确认自己便是圣王的后世子孙,也确信先祖同意留下来接受侍奉。“王公宫”向来不大也不显赫,倒是近年来一番整修,容光焕发站在宽阔的市府大道边上。去年,又因“益中花园”在旁兴建,开发商捐资再让它又一次改崭新的面貌傲然挺立。
“武府宫仔”在后保社口,很早前就破败了,灰红色的纸钱香炉冷冰冰的,小时候依着口误称它“母母宫仔”。几个破烂的神像被清除后庙里住了人家,近几年被翻修得像“美山殿”。去年也幸逢“益中花园”的兴建迁居重建在“王公宫”的身旁,沿旧称“武府宫”。
“土地公宫仔”原在袁厝与后保交界的坡上,透过木栅栏看得见土地公、土地婆老俩口子坐在阴冷处。多年前这宫仔整理了一下,又有位孤寡老头以此为家便显得有些暖和的气息。如今“土地公宫仔”不在了,随袁厝的老邻居们搬迁去到“岳阳小区”住上了一套两房一厅。“土地公宫仔”旧址正在市府大道上离“王公宫”很近的那处最高的路面当中。
“美仁宫”是前保人的社神祠。听老人说,早先建筑也很粗糙,但临着龙船河边的一池清水竟也是一处“美人照镜”的佳境。厦禾路修建后,前保人集资以西洋式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洋楼,加盖中国式的屋顶作为地方的神祠是很有现代意识的。这是在厦门沦陷于日军手中之前的事情。宫内供奉的大道公、妈祖婆、关帝爷的神像并无特别之处,精彩的是粉壁上墨线素描的神仙,或乘龙驾凤,或跨鹤骑麟。可贵的是那民间艺术家还是美仁前社的自家人,我幼年时有幸亲睹这童颜鹤发的老人在榕荫下挥毫作画。
“美仁宫”的荣幸是它的大名彰显贵为一片地域的泛称。而它的大不幸是最终名存实亡,自文革被摧毁之后便无重生的时日。在长期沦为居委会铁工作坊的烟熏火烤之后早巳蓬头垢面又遭了火灾。后来拆除了,重建新楼先后改成幼儿园、老人娱乐中心、小区文化中心……产权归属思明区政府。“美仁宫”仅借用其底层的西屋再继续“美仁宫的故事”。
最显赫的往往最先衰败,这似乎是难逃的命定劫数。
假如朱熹真的曾经在遥远的宋代登临白鹤岭赞美过筼筜港边、龙船河岸、尾头山下的尾头社渔耕人家,那幅古典诗情写意画在20世纪初厦禾路开通之后就巳经翻过去了。而不必多加考证的文革期间的“围垦筼筜港”确实是根本地改变了“美仁宫人”,尤其是“后保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果你曾经有幸目睹过当年被围堵干涸的筼筜港海滩,辽望那黑蓝蓝的滩涂在烈日下暴尸,板结龟裂、臭气熏天,你会有一种天灾降临、世界末日的战栗。这片被当作“人定胜天”荣耀象征的土地,人们曾经期望它完成“五谷丰登”的地主式的宏愿。而世事多变,它并没有出现“喜看稻菽千重浪”形势一片大好的美景。在茫然不知所措的“后事处理”中它变成了你抢我夺的无主的财富,任人跑马圈地,随意瓜分,真应了“暴殄天物”的说法。
听《渔舟唱晚》,看“筼筜渔火”,是不渔者们高楼饮酒吃海鲜想象出来的“渔家乐”图景。出没风波里毕竟是流汗、流血又卖命的艰难营生。即便筼筜港未曾改天换地,后保人也不可能再指望种石蚝、拖浒苔、洗蚬仔以期丰衣足食;蚣代、甲锥螺,蜅蛙、豆仔鱼……都不过是配稀粥的小菜一碟。所谓“抹水抹汁,万世毋捏(泥水沾泥的生营一辈子不得翻身)”说的是单靠手脚勤劳在稀泥浑水里捉摸、打捞,几代人都要一直穷下去。你去问一问社里人,尾头社三角头哪座高楼豪宅是拖浒苔、洗蚬仔建造的?改变生存环境,改变生产方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筼筜港的地理环境是改变了,筼筜港沿岸人们的生产方式也改变了。也许,老厦门人、新厦门人都应该赞许改造了筼筜港创建了新厦门的举措。但是——如果我们有权利说“但是”——筼筜港的改造是先死于七手八脚的乱棒之下,再转活于手忙脚乱的抢救之中的。如果当初决策者们有一种现代的社会意识、发展意识、环保意识、审美意识,在今天土堤横断筼筜港的位置上架设三座桥梁,南北两边石砌驳岸,海水潮潮汐汐一天两回自由呼吸;横横桥上车水马龙,直直港里百舸争流。一座壮美如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厦门不是可以得来不费大功夫么?
……历史没有假如。厦门或许只能得到她命定能得到的这点福分。
卖朱李仔的“胡须的”
今天,年近六十的美仁宫人如果谁不认识“朱李仔胡须的”,那他怎么能叫做“美仁宫人”呢?“胡须的”是我们儿童时代里最亲切的人。“胡须的”的尊名大姓我们都不知道,但是,直到今天我只要向同代美仁宫人一提起“胡须的”,没有人会忘记他。
“骗囝仔吃,吃鸦片,没吃不过瘾”,当年这句童谣是专骂那些骗小孩子钱的小买卖生意人的。“胡须的”从来不“骗囝子吃”,一分钱一分货让你实惠不吃亏,小孩子爱买他的东西吃。他卖的“朱李仔”不是今天那种“啫喱仔”水果冻,是鲜果的腌制品。半边桃、半边李、甜橄榄,甜洋桃、蜜柚皮……浸泡在他那只红色木箱的玻璃格子里。红是红,黄是黄,水灵灵的形色俱佳,甜脆爽口。用竹夹子镊出来,小纸片托上交给你,那纸片是平展的香烟壳裁开的。
善良和蔼的“胡须的”不是美仁宫社里人,但社里大人小孩都喜欢他。听说他家住第七市场的关隘内,每天午后才来,生意就做孩子们午饭后、上课前这一黄金时段。美仁宫前大榕树下的那一片红砖埕是孩子们下午上学前的乐土,所有小买卖此时云集此地。两棵大榕树树荫之下的午后一片小朋友们的鶯歌燕舞。小朋友最盼望的还是吃“胡须的朱李仔”,午饭后早早就从家里出来,殷切地等他,有的还跑到马路边上去张望。远处尖厉的唢呐声动人地传来,孩子们欢呼雀跃:“胡须的来了!
胡须的来了!
”络腮大胡的“胡须的”慈祥地笑着,肩挎红色朱李仔箱,左手提木架,右手持唢呐,弯着腰身在孩子们的簇拥下不停地同社里人打招呼,穿过熙熙攘攘的美仁宫口,停在红砖埕他固定的位置上,圣诞老人般地赐福童心来了。
多少年月已经过去,多少世事曾经经历,在这已过花甲之年,每当我听到日本那首歌谣《邮递马车》唱着:“听吧,听吧,听吧,听吧,越来越近了,邮递马车,幸福的车……”我便想起童年时盼望“胡须的”,见到“胡须的”那种欣喜。
冬天里,“胡须的”兼卖烤鱿鱼。敲打松软的鱿鱼干不知是怎样的精心慢烤,散发着诱人的浓烈香味。烤过了再剪成条状用手摇齿轮机“嘎嘎”地压成条纹细密的瓦楞样的波形薄片,再剪成小方块,一块2分钱。吃过“胡须的”烤鱿鱼,念念不忘到今天。现在不论买包装精致的舶来品还是如法炮制的自产货,一进口就知道不是那回事。2007年我在台北,淡水镇上街边有卖烤鱿鱼的,香里带甜地诱惑人,一看是成团的鱿鱼丝。忍不住童年记忆的催促买了一包,才入口便知道又是另一回事了:手一捏,是粘的。嘴一吃,是甜的。童年记忆中的那个烤鱿鱼干的芳香竟消失在遥远过去的岁月中了。是小时候的嘴巴容易搪塞,还是“胡须的”做小吃真是好手路?忽地感到人生匆匆,老已临身心惶然。
俗话说:胡者不仁,麻者奸臣。而他一脸络腮大胡的朱李仔“胡须的”却是让我们当年美仁宫的小孩子这般的怀念,怀念到大家都变成了比当年的他还要老的老人。
文革兴起,学校关闭,社会动荡。美仁宫被“破四旧”了,恩主公、妈祖婆一一被赶下神坛,美仁宫变成了铁工厂。榕树下宫前红砖埕的小买卖日渐稀少,朱李仔“胡须的”阿伯也不再来了,半个世纪转眼过。
一轮甲子的人生早已过去,仍时时怀念“胡须的”朱李仔,怀念朱李仔“胡须的”阿伯。“胡须的”老伯何处去?想必是早已归天。如若健在,应是百岁寿星,银须飘飘,真真一位圣诞老人了。
老榕树
美仁宫的老榕树有多大的树龄?我不清楚,从小到老看着它们就好像一直这么巨大、这么苍老,将近六十年要过去了似乎什么也没变。1959年大台风横扫厦门岛,一夜之间,拔树倒房,船毁人亡,而美仁宫的老榕树安然无恙。1999年“十四号台风”正面袭击厦门岛,天旋地转摧枯拉朽,但是美仁宫的老榕树毫发未损。今年,台风“凡亚比”仅仅从厦门擦身而过,美仁宫的老榕树就残肢断臂了。
半个世纪前,美仁宫四周无一高楼。十几年前,美仁宫四周也还无一高楼。而如今,美仁宫头顶上是那么一小块被高楼大厦切割成多边沿、多角度、多缺口、多形状的天空。百多米高的“银聚祥邸”、几十米高的“冠成大厦”并排毗邻,巍然耸立,雄视着被斩劈的两株老榕树一大堆垂垂挂挂的枝枝杈杈。邻居老阿姆说:“楼起得这恁高,巷子风这恁透,老榕树不倒也得倒!
”
美仁宫是前社人的社神祠堂,一座戴着中国琉璃瓦屋顶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洋楼。宫内供奉的恩主公(大道公在此的尊称)、妈祖婆、关帝爷的神像。粉壁上是墨线素描的神仙,或乘龙或驾凤,或跨鹤或骑麟,优雅飘逸。屋檐下悬着大块额匾青底金字楷书“美仁宫”。宫前的大院,东西各有一株老榕树,两株老榕树树冠交叉拥抱联成一片,庇护着树下的老人孩子,这里是他们的快乐天地。黄昏来临,归巢的八哥鸟一群又一群欢叫着没入浓荫。夏夜,社里的男人、小孩子一头枕一领席在树下酣睡。半夜里醒来,望着头上那片黑色的像地图一样的树影,手伸向两边,遍地是豌豆一般的树籽。这是美仁宫乡土平常的夜色。清晨,美仁宫墙角上的大喇叭响起南音《梅花操》乐曲,厦门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音了。傍晚,《马兰花开》响起就是要“天气预报”了。1958年炮轰金门之后,《梅花操》换成了《厦门颂》:“厦门,厦门,你是英雄的城,千里海涛万里浪……”文革来了,大清早响起的是《东方红》!
美仁宫在文革中被摧毁之后长期沦为居委会铁工作坊,烟熏火烤蓬头垢面,西边的老榕树在一次火灾中烧去了一大截。文革后,破烂不堪的美仁宫被拆除,重建的新楼先后改成幼儿园、老人娱乐中心、小区文化中心…… “美仁宫”仅借用其底层的西屋摆放“恩主公”再继续 “美仁宫的故事”。这里是早已没有神祠“美仁宫”仅存地名的 “美仁宫”……
最近几年里,十八层的“冠成大厦”在它西边平地而起,一南一北前后两座大楼近百米的中庭。中庭向西连着“佳韵园”的中庭。再向西,接上“亿力花园”的中庭。继续向西,又接上另一座“亿力花园”的中庭,直抵斗西路口,形成一条几百米长的“穿堂风”大风道。三、四十层,百多米高的“银聚祥邸”雄赳赳气昂昂地挡在它的东南面,这是老城区最高的商住豪宅、厦禾路上最威风的标志性建筑。“银聚祥邸”与“冠成大厦”相间隔的缺口正直对着这座早已不是社神祠堂 “美仁宫”的四层楼房,楼房前是这两株老榕树。正在施工的“皇家御城”将以五十几层 “福建最高住宅楼”如山的巨无霸在“美仁宫”的北面遮天蔽日!
“凡亚比”来了。它只是羽翼末梢从厦门轻轻扫过。
风从东南方向刮过来,从“银聚祥邸”与“冠成大厦”之间的缺口杀向“美仁宫”。旋转的台风一头撞进这“美仁宫”三岔口,横冲直撞,左奔右突,愤怒咆啸。风在这里被强行分切两路,一路顺着“冠成大厦”与“美仁宫”之间的巷道向北杀去直扑美仁后社。另一路左拐向西,这股狂暴的“穿堂风”顺着一座座高楼中庭相连接的几百米长的风道呼啸而去。无数风的巨手撕扯着首当其冲痛苦挣扎的两株老榕树,一把又一把地把它生吞活剥……
老榕树终于断了。这座早已不是美仁宫的“美仁宫”任凭滂沱大雨的冲刷。雨停了,没有大树遮蔽的“美仁宫”显现出四个平日不见的铜板大字:“市民学校”。
作者简介:庄南燕,笔名雪狼,厦门人,1951年出生,毕业于福师大,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勤于笔耕,擅长刻画本埠底层人物。
LOOKERS鹭客社 守望共同的尘世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