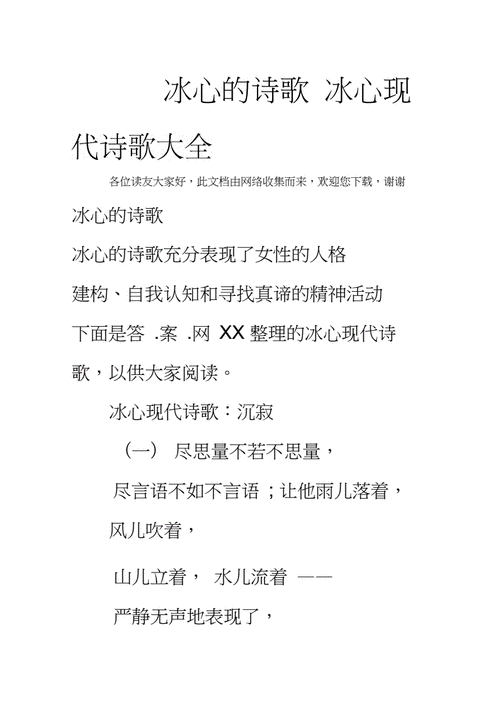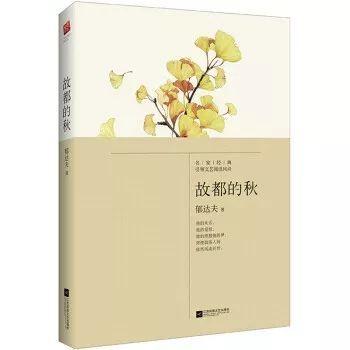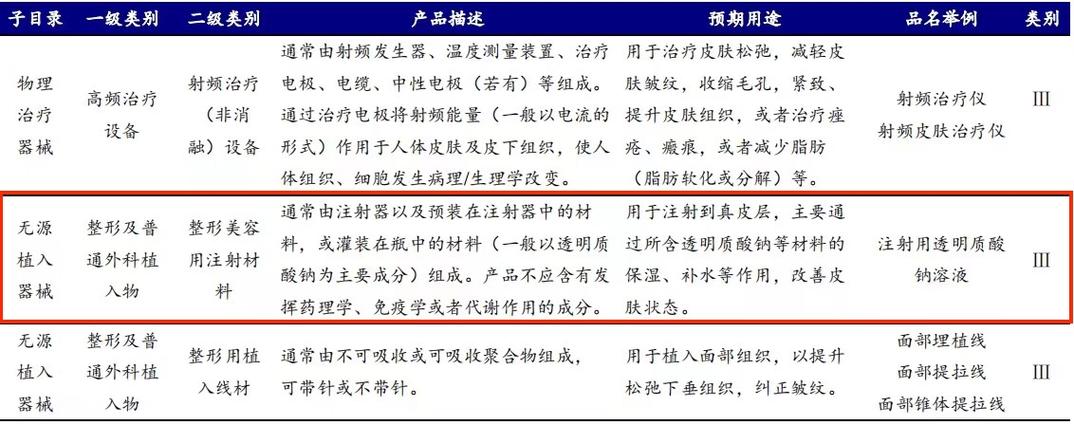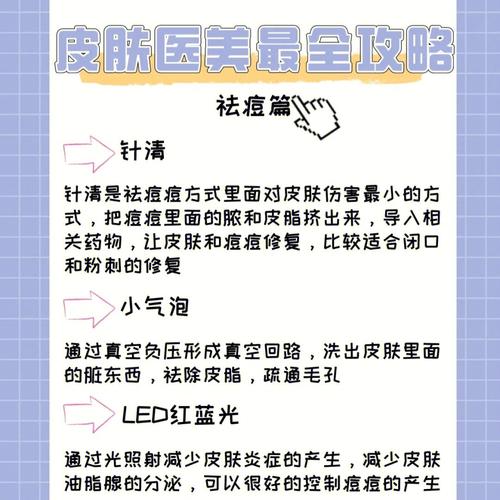长白山的明月_生命中的诗歌(詩歌我在明月)
吴景慧。
其实与景慧兄相识已经很久了,久到足有二十五年的时间跨度,人生又有几个二十五年呢?

那个时候,我在山东东南隅的莒县写诗,他在吉林东南部的长白县写诗。各自在一座小县城里,守着几条熟到不能再熟的街道,纠集起几个铁到不能再铁的伙伴,扯起大旗,咋咋呼呼,一个个诗社文学社就横空出世,挤到了中国文学史中去。
当然,这个挤到中国文学史中,只是我们自己的臆测,除非这本文学史由我们自己书写(我倒真有这个想法),否则,臆测成真的日子,恐怕我们这一代是看不到了。
但那是个物质相当匮乏、精神却高度饱满的时代(我一直认为中国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年代),仅凭想象,就足以让我们热血沸腾。我是个初出茅庐、少不更事的小伙子,其时仅十余岁,为了不着边际的理想,热血沸腾也就罢了,难得的是,比我大了足有十多岁的景慧兄,居然也热血沸腾,激情澎湃地在那个边陲小县组织诗社,出版诗报,让诗歌借着长白山风,猎猎飞扬,飘散到全国各地的民间诗歌组织中。
后来,也就是2012年,我在长白县的夜色里,与景慧兄深聊,知道他之前当过兵。军人性格,当为其行事行文基础了。
当时我曾激情澎湃地创立了一个新古典主义诗歌流派,广泛联系国内诗歌界有相同诗歌审美趋向的诗人。那个时候没有家用电脑,所有的联系都靠书信,鸿雁往返,带来的不只是诗的张扬,更多的,是因僻处小县所带来的孤僻落寞,会缘于雁书的往返,而得到缓解。
我如此,比我所处地域更偏僻的景慧兄,亦当如此。
当时,我曾提出做一次中国新古典主义诗歌联展,十家民间及非民间的报纸同时推出。这是一个比较浩大的工程,为此,我在部分城市已经组织建立了中国新古典主义诗歌联盟的分盟,十家报纸,也确实有几家已陆续推出了联展的版面。
十家报纸中,一家就是《长白文化报》,吴景慧主持。
那是二十五年前,是诗歌让我与景慧兄缔结了友谊,是诗歌让我们相互听到了彼此的心声。这友谊,这心声,是如此纯粹,并在随后的岁月里,逐渐沉积,成为一生的醇厚珍藏。
当时,我为联展写了一首七律:《书于中国新古典主义诗歌联展之首》:
结盟同谱大风篇,江山尽入指顾间。
马饮五湖明月在,诗传九州古风还。
胸中肝胆共酒热,天下英雄与君先。
谁谓鱼龙真寂寞,扬波犹上九重天。
而今回读,唯有苦笑而已。五湖明月犹在,九州诗风,已靡然而成别种风情;胸中肝胆,早与酒俱冷;天下英雄,亦绝响空谷。鱼龙犹在渊深,九重天的梦想,久已泯灭无迹。唯有寂寞永在,千年前如此,千年后也将如此。
寂寞十余年,花开复花谢。家用电脑普及了,联系反而减少了,用笔一字字写下的热情,也逐渐在键盘前消解了。
十年前,景慧兄到浙江,途经日照,我开车陪他去看海,车停在海边。在万顷碧波前,我刚刚说完日照的蓝天碧海金沙滩,也刚刚听过景慧兄描述的长白韵致,回身上岸,傻眼了:车窗玻璃被砸,景慧兄的包被从副驾驶座上偷走。
面对景慧兄的微笑和安慰,我惭愧在了这片蓝天碧海金沙滩间。小城日照的形象,也被这破窗一击砸得粉碎。
一转眼,又是多年,终于,有机会自驾车携妻子女儿远赴长白山。那里不只有壮美的山水,更有让我不舍的友情,以及,久违的诗歌。
至今,眼前仍清晰地看到那片长白的夜色,在那个小县城的边缘,在与朝鲜城市仅隔十几米的鸭绿江边,我与景慧兄一起,边走边谈,谈诗歌,谈人生,谈理想,当然,也谈理想破灭后的落寞。
在滚滚红尘中挣扎求存,一路走来,市井烟尘,早已替换了诗骨。没想到,在这片清清江水的边缘,又依稀重新看到了二十多年前的自我模样。
十月的长白,风已很冷。那个晚上有月亮,在长白山之麓,鸭绿江之畔,碧空如洗,万里澄清,月亮显得分外大,分外明。
对岸的朝鲜城市,一片寂灭,几点灯光,鬼火似的闪烁,时有背枪的士兵从对岸的鸭绿江畔走过。我不知道我们说话的声音他们能不能听到,两岸相距,仅十余米。
那天晚上,在我们江畔漫步之前,景慧兄夫妇在一家小酒店请我一家吃酒,景慧兄后来写了一首诗,其中几个句子,不分行说得就很明白:“以茶当酒,几盘特色小菜,在来来去去的推杯换盏中,炒热了脸颊,激活了神经,让热情洋溢的鸭绿江,成为此时最好的见证。”
酒后的江畔漫步,边疆清月下的江畔漫步,由此烙印为我一生的珍藏风景。景慧兄就是这片风景的中心。
随后几天,与景慧兄连续交流,对此,景慧兄在他的诗里也有记录,我仍然把这些诗行连缀起来:“古迹、风光、典故、传说,在话锋和游历中翻转腾挪,被感染成色彩,印在心底,成为永远的铭记,和一生抹不去的风景。”
离开长白县的那天清晨,怕景慧兄大早来送,我在六点时就给他发短信:我已离开长白,你不用过来送了。一分钟后,接到景慧兄的回复:你的车就停在宾馆院子里,你步行着离开长白吗?我就在楼下大堂等你,为你饯别。
又是江畔早餐,饭后握手,挥手。车开远了,反光镜里,犹见景慧兄立在饭店前目送的身影。
那是长白山的十月,晨风中寒气袭人,但温暖溢满心头,至今,永远。
时间又过去近两年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们的联系依然不算密切,但我知道,数千里外的长白山麓,有一位兄长,他一直在默默关注着我,而我也同样,对数千里外的长白山麓,有着牵连不断的挂怀,这一缕友谊的牵挂,成为我心中不湮的阳光和温暖。
几天前,景慧兄寄来他的新著诗集《低飞的音符》。我在收到集子的当天晚上,就基本通读了,还是那样的古典清雅,意韵绵长。很感慨,二十多年的时光,已将我的诗情消磨殆尽,而年龄大我许多的景慧兄,居然仍能维持同样的诗歌热情不减,并且在写作质量上,逐渐呈现经典化趋向,这该是怎样一颗纯净包容的诗心。
诗人吴景慧。当他的整个人都成为一首诗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无法再具体地去分析、评论哪一首作品了。因为,景慧兄与他的诗,已经融为一体了。
正如那夜,升起于长白山脉的月亮,它冷冷的清辉洒向大地,这是无法割裂的明亮和光辉啊!
2014年5月19日中午,急就于日照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