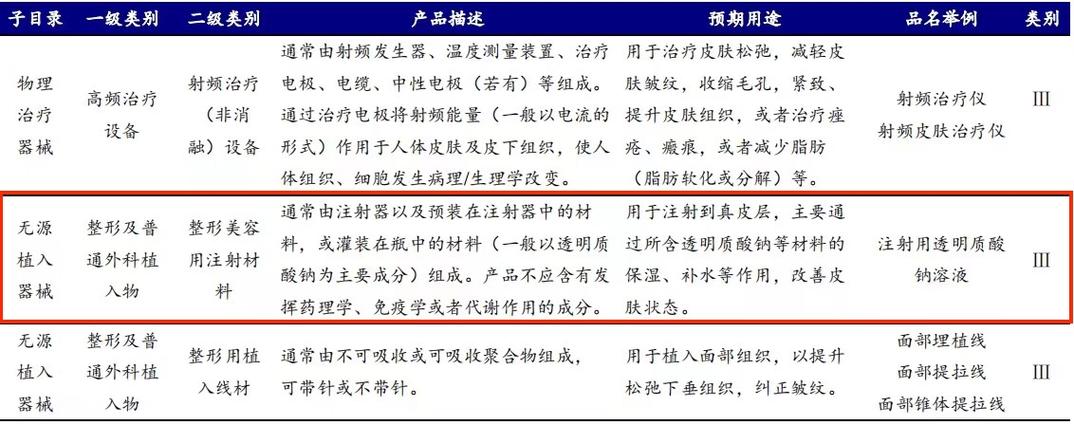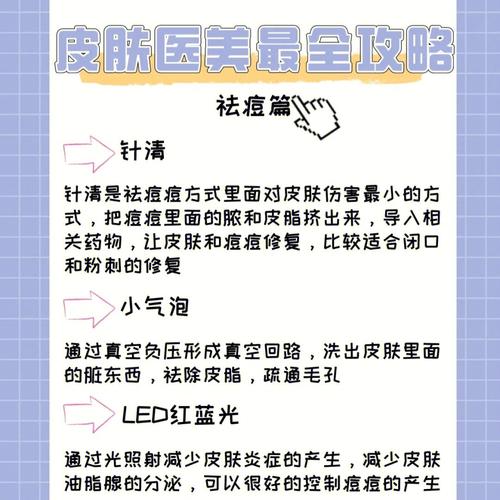18年多次独闯非洲!看看她眼中不一样的非洲女性(女性眼中女人)
一个独闯非洲的女人,
18年来,她多次深入非洲,在寻找什么?
在世界最陌生的国度,她又有怎样的遭遇?

在她眼里的非洲女性,又是怎样的?
自由摄影师梁子非洲探险,
带你了解不一样的非洲女性!
提起非洲,你脑海中是什么画面?也许是广袤的非洲大草原,也许是跨越三千多公里的动物大迁徙,也许是世界各地的马拉松赛道上疾驰如风的领跑者。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正式在北京开幕,关于非洲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你了解多少?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女性,你又了解多少?
作为中国第一位独自深入非洲部落进行人文调查的女摄影师,梁子女士多次独自前往非洲,进行人文调查及拍摄非洲人的生活方式及生存状况。在她眼中,非洲的女性是什么样的?
我对非洲女性的印象
作为一名女摄影师,我更喜欢观察与我同类的非洲女人,她们的活法有沉重也有生趣,她们的心境平舒淡漠,终生辛勤操劳,却乐在其中。从2000年至今,18年过去,我依然对非洲情有独钟,许多人问我,是什么如此吸引你,我就说说自己认识的非洲人。
在非洲的村落,女孩儿出生后,一两岁时自己爬,三四岁时小尾巴,四五岁时带弟妹,六七岁时洗锅碗,七八岁时拾柴火,八九岁时去打水,九十岁时烧饭菜,十一二岁订婆家,十二三岁为人妻,十四五岁为人母,四十岁时当祖母。直到死,也不会像男人那样有资格葬在自家院落。因为,女人永远不会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女人结婚没自主,父亲看中的男人就是她的丈夫。在不少非洲村庄,婚后妻子生了两三个孩子后才能出门。接下来一生要伺候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她们没有发言权,没有选择权,没有反抗权,没有放弃权,只有接受和承受。
女人活得很琐碎,每月一次的“倒霉”,唧唧喳喳的话语,啰啰嗦嗦的嘱咐,老人与孩子,吃喝拉撒,男人的脸色,这就是她们的一生。这些女人,大部分没有接受太多的教育,但她们的心襟却异常的宽阔。面对一无所有的贫穷,活得如此从容;面对疾病,她们没有因不可医治而困惑难耐;面对死亡,如此超然的淡定。人生的生老病死,在她们的意识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她们的一生色彩斑斓,从头发丝到脚指甲缝都埋藏着精彩的故事。
非洲女人的欢快
在非洲,见过穷的,也见过穷开心的,却没见过穷得一无所有,却乐得欢欣鼓舞的。
特瓦族来源于俾格米人,是非洲最原始的民族。他们世代生活在热带雨林中,是赤道人种的一个特殊支系,他们的生存方式,一切与生命有关的,统统源自于大自然。千百年来,他们祖祖辈辈已经完全适应了森林生活,并依靠大自然生存早已形成了独特的体魄、意识和身体条件,他们身体强悍,意志顽强,野性十足。特别是他们的消化系统、味觉、牙齿、手脚等都形成了特异的自身结构。一旦离开森林,也许会因身体无法适应而患病导致过早地死亡。森林里的俾格米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拥有顽强的生命力,是一般人类所无法比拟的。
而布隆迪的特瓦人,单从体貌上看,已经很难找到他们的俾格米人矮小的特征了,这些特瓦人被人们看作是已经“进化”了的俾格米人,原本生活在布隆迪与卢旺达边界的森林里,随着国家对森林和动物的保护,不准人们在森林里狩猎。从此,这些特瓦人陷入了被剥夺了谋生方式的痛苦中,因而造成了生活的窘迫,也带来了严重的贫困。不少人因为感到绝望而靠酗酒度日。
他们希望能够坚守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但他们在森林里捕杀动物的行为,越来越不受人们的欢迎。于是,他们不得不渐渐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而这并非一两代人能完成的根本转变。从狩猎到农耕,从食肉到粮食,他们艰辛地生存着、适应着、也不得不贫困着。
然而事情并非我所想像得那么悲观。当我来到特瓦人居住的村庄时,简直令我惊呆了。
一群脸上写满阳光的女人,伴着欢快的歌声,有的坐在地上,有的身背孩子,有的站立着,所有人都在做着共同的事情——捏泥罐。每一个在场的女人都是边唱边干着活儿,她们充满了自信,洋溢着欢乐。那场面,又像是自然状态下的劳动,又好像在编排一场歌剧。
她们把欢乐注入了血脉中,流动着、沸腾着,按我们的话说,怎么看都觉得人人像打了鸡血,兴奋难耐,快乐不已!
这究竟为什么?快乐的来源何在?我问身边的酋长:“今天是什么日子?她们怎么如此高兴?”“你觉得奇怪吗?我们永远都是这样。”他轻松地笑着说。
这一带的特瓦人主要靠捏泥罐谋生,随着布隆迪这些年人口急剧上升,土地越来越紧缺。而这些长期靠狩猎生存的特瓦人又不会耕种,没有经济和农作物来源,只好靠手工艺换取金钱,再用钱购买食品。
“一个泥罐能卖多少钱?”我问。“四五百布朗(相当于人民币三四块钱)。”酋长说。
这么少的钱,在食品匮乏,物价高昂的布隆迪,连一顿普通的饭都吃不上,他们怎么养活一大家人?事实确实是,他们每天都经受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困苦。
好在,不会耕种的村民很幸运,村后有一片岩灰状黏稠的泥浆,妇女们把泥捞出来,用双手捏制不同大小和形状的泥罐,之后,在阳光下曝晒,泥罐干了之后,就可以当放置水、粮食等器皿。
就是这么一小块地,解决了她们的谋生问题,一旦有吃有喝,她们的生活也就无忧无虑了。非洲人就这么简单,而简单能使人快乐。
非洲女人的大气
我之所以喜欢把自己放在非洲村落的女人堆里,是因为这些女人不论从外表还是内心,简单又有趣儿。多彩的服饰,叽喳的唇舌,琐碎的是非,老人与孩子,吃喝拉撒,男人的脸色,这就是她们的一生。
最为令我震撼的是,这些女人们没有接受过太多的教育,但她们的心襟却异常地宽阔。面对一无所有的贫穷,她们活得那么从容;面临疾病,她们没有因不可医治而困惑难耐;面对死亡,如此超然地淡定。人生的生老病死,在她们的意识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她们强大的精神世界,时时感染着我,这也是让我一次次走近她们最重要的理由了。
60多岁的“马滚蛋你”,生了13个孩子都相继离去,哈莉玛的孩子被接生护士用剪刀夺去了生命,以及艾滋病老师泰必斯,临死前对这个世界坦然又淡定的神情。她们没有抱怨,没有恐惧,也没有放弃。再艰难的生活,她们接受着,过的有悲伤也有欢乐,重要的是,她们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信心,带着一份平朴的心活在现实中。
我尤为爱那些劳动的女人,她们生动、有趣、开朗、大方,在关键时刻显露的精彩,是男人们永远无法效仿和比拟的。非洲女人的精彩在于她们的简单和豁达。
记得我曾经问过一些女人:“你们觉得自己快乐吗?”我原以为她们会有力地回答:“快乐!
”但事实上,她们快乐只占一半。问其不快乐的原因,因为时常被酒后的丈夫拳打脚踢。而快乐女人的解答是,丈夫从没打过她。看来女人的幸福来自于男人,这也是女人亏欠自己的地方。
非洲女人的智慧和勇敢
在有些状况下我们所谓的教育,和一个人的生存能力没有什么关系。把一个被现代知识装备后的人放在那些相对原始的部落、村庄,他们未必能生存。但是,一个人的经历丰富后,这些经历会让她冷静,让她有判断,从而拥有生存的技能。
教育给人的是间接的经历。那些村子里的女人们她们有许多从自然得到的直接经验,在我们无法想象的困境中,她们可以生存下去。我们可能从生存手册上学到如何应对沙漠险境,但面对突如其来的沙尘暴时我们仍然不免惊慌。 然而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就会好很多。森林、砍刀、趿拉板、女人,这就是聚集在莫卓口一人身上的所有元素。虽然她并不刻意地潇洒举动,令“躲藏”在镜头后面的我,多少有些自惭。
莫卓口个子不高,话语不多,表情平淡,看上去并不强悍,但她与黑非洲的其他女人一样,都有个共同点,一颗强盛的内心。在黑非洲,女人明显有一种生命力,这种力量在生活中随处体现。比如,硕大的森林,大面积的杂草,许多时候都是由女人带着她们的孩子一点点清理,女人不厌其烦地一个接一个生孩子,耐心地哺养孕育一个个脆弱的生命。要在大自然中采集原料,为一家老小烹调饭食,也许,她们在森林采集原料时,还会发现新的草药。劳动的女人有眼光,有智慧,她们身上具备着生命的能量,这种能量只有在劳动过程中才能体现出来。
我跟着莫卓口,从她家走到她的种植地,行走在雨林里,起初无声无息的,走得很沉闷,加之不间断的雨水,森林里的光线就更加暗淡。我跟在她身后,越走心里越毛,想着万一从哪棵大树后面猛地蹿出个威猛动物怎么办?
我问莫卓口:“像这样的原始森林,一定有很多大动物吧?它们会袭击人吗?”
她笑笑说:“我从小跟着我妈在森林里干活,很少见过大动物,你不用害怕。”
“难道这里没有老虎?狮子?黑熊?”我问。
“这里最多的是植物,而吃植物的大动物不多。所以,那些大的食肉动物很难生存,有时会有鹿、刺猬、大象、野猪,最多的是猴子和蛇。”她说。
我们走在没有道路的森林里,尽管我不断地查看随身携带的指南针,但还是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晕”,根本分不清东西南北。都说原始森林是绿色沙漠,没有真正走进这里,无论如何也感觉不到它的恐怖和人类在其中的渺小。现代人坐在装修明亮的写字楼里大肆倡导,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真的把那些高调倡导者们扔在这茫茫绿海中,别说和谐了,不尿裤子就算他是有胆的人。
在森林里看植物是最有趣儿的事了,一些巨大的树木,它们生长时间很长,树的根部就开始往地面延伸,形成了一个个放射的根翼,这些根翼能帮助支撑通天大树,还能使大树吸收更多土地的养分。
我看见森林里还有不少老藤,它们有的缠绕在大树上,很像一对缠绵的情侣,有的像个垂帘,尽显神秘不可莫测,还有的悬在空中,又像是绿色的瀑布。我想,这些生长在雨林里的老藤也够有韧性的,也许是为了寻找生长空间,迫使它们不得不利用大树的位置来解决自己的生计吧。
其实,非洲森林里的女人,大都没什么文化,但是她们在生活中积累了大量的生存知识。她们从出生就与原始森林、各种疾病、特殊气候、蛮横动物、繁杂植物和谐相处与顽强抗争。她们有着坚强的意志,勇敢的胆识。她们在有限的生命中,不断的创造、认识,体验和传播。
在非洲村落中的女人们身上,我看到城市里受过教育的我们很少有的生存智慧。
非洲女人对死亡的坦然
许多非洲女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坚定的信仰,在她们的一生中,从孩提时代就要接受亲人的离去,意外伤害,疾病袭扰,为此,生生死死对她们来说,是如此的自然。
在此讲一讲艾滋病女教师泰比斯的故事,她临死时不是交待家里的后事,而是嘴里蹦出来的都是有关大自然的单词,令我非常诧异。
我很早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生存目标:今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成为一个自由快乐、身心健康的人。于是,我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着。
我从小生长在部队大院,16岁当兵,原本可以在骊山脚下的部队疗养院过着舒心的日子,却自己要求去了青海高原,两年后又主动请缨奔赴云南老山前线参战,成为了一名战地摄影师,战后立了功,参加了英模报告团,后来又悄然进了西藏。两年的西藏高原生活,使我对在自然状况下生活的人多了一份亲近感。再后来,尽管不到28岁的我,亦成了一名少校军官,但是为了追寻自己心中那份自由快乐的生存目标,我脱去了戎装,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人,开始了我的独自远行。
非洲是一个很容易让人热血沸腾的地方。每一次非洲行,都像是一场心灵净化之旅,在感受了“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之后,它教会了我如何去爱社会,爱生命,爱现实。它还让我学会了承受许多常人难以面对的灾难和平淡,以及对突发事件冷静的判断力和处事的果断性,最重要的是,拥有一颗坚强的心,远比无病呻吟的人活的更加自信。
把一个个遥远的人们和那些感动的故事装在心里,距离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我想,这些都不是坐在都市咖啡厅的阳光下,读几本书就能获取的生命力量。走出去,相信你会变成一个敞亮而有大爱的人。
梁子
自由摄影师
梁子16岁当兵,毕业于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系。
中国对越作战军中唯一一名战地女摄影师,曾荣立二等功。
中国第一位独自深入非洲部落进行人文调查的女摄影师,第一位进入驻阿富汗坎大哈北约军营的中国女摄影师。
自2000年至今,多次独自前往非洲,进行人文调查及拍摄非洲人的生活方式及生存状况。
编辑:撕纸小妹、巴塔木、晓静